Kathryn Joyce在《新共和》杂志发表文章,在美国的保守派思想中,现在又催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集体主义,他们誓要将国家带回到神的面前,即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然而,这群人对基督教的 教义知之甚少,也不强调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教义,对他们来说,基督徒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在思想上跟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契合,这是一股值得拉拢的力量,仅此而已。
11月初的一个周一晚上,在奥兰多希尔顿酒店的一个地下室宴会厅里,四位保守派知识分子——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新保守主义者、一位“政治天主教徒”和一位“我为什么离开左翼”的家伙,坐在台前,手拿饮料,讨论着保守主义的未来。
一架无人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为一位小组成员的YouTube节目收集素材,扩音器里播放着清晰的背景音乐:美国乐团Sister Sledge的赞歌《我们是一家人》。
这是全国保守主义会议(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下文为NatCon)的第二个晚上,一次右翼学者、作家和智囊团的聚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一直认为,联合宗教保守派、反共人士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旧里根主义联盟已经结束,一些新的共同愿景必须取代它。
总的来说,会议的发言人阵容似乎并不像一个会团结在一起的集团,他们的想法也不是特别新颖。
有关于新词汇的抱怨,对需要强化摔跤课程的“豆芽男孩”(“豆芽男”是网络中经常用来形容缺乏阳刚气质的男性的一个贬义词)和大学“由女性主导”的哀叹。
有关于将避孕定为犯罪并可能恢复麦卡锡主义的提议(用不充分的证据公开指责对方政治上的不忠或颠覆,或者是用不公平的调查或指责来打压反对人士);声称“觉醒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比白人至上主义”更大的威胁;发言人多次计划搬迁到“佛罗里达自由州”;还有相当多的“加油布兰登”(2021年兴起的一个政治口号和网络梗,是针对拜登的教委婉的脏话)。
与会的几位大人物都在争夺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民粹主义右翼领袖的衣钵,包括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和乔希·霍利(Josh Hawley,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的同事、俄亥俄州作家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他套引尼克松总统的话宣称:“教授是敌人。”(尼克松的原话是:媒体是敌人) ,还有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国际队伍来到这里,希望精心打造一个“国际民族主义联盟”。
尽管会议最大的头条新闻是霍利在开幕式上的声明,即左派对男性的战争造就了沉迷于色情的一代人,但会议的核心议程是周一晚上的非正式讨论,与会者包括以色列政治理论家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英国作家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美国保守派特约编辑索赫拉布·阿玛里(Sohrab Ahmari)和政治谈话节目主持人戴夫·鲁宾(Dave Rubin)。
作为主办这次会议的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主席,哈佐尼主持了这次会议。正如一位听众令人不安地说的那样,他宣称,会议的目的是在右翼混乱的派别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看看有没有可能“团结右翼”。
在会议上和会议后,这个问题激发了一种紧迫感。尽管有很多关于民主党混乱的评论,但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就是保守派才是软弱的、被围攻的,在长期失去文化支持之后,他们现在还被剥夺了政府权力。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莱曼·斯通最近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任何天然联盟,也没有通往国家多数的明确道路,保守派没有明显的前途。”
但哈佐尼提出了一个改变现状的建议:鉴于基督徒占多数,可以宣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应由基督徒支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规范。
他说,可以为少数群体“划出一些区域”,但不能有一个中立的舆论,在这种舆论中,对多元化的支持压倒了多数人只想看到自己的文化被彰显的愿望。
专家组能否就此达成一致:不积极迫害少数民族,同时让大多数人控制舆论?阿玛里建议采用匈牙利的模式,这个国家禁止同性婚姻和同性夫妻收养孩子,禁止在法律上承认变性人,最近还禁止与未成年人分享LGBTQ内容,但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阿玛里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得到了很好的待遇,不会被排斥,也没有受到任何压迫。”
政治谈话节目主持人鲁宾说道:“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问题,我们这里就有两位小组成员是同性恋。如果哈佐尼提议的公共规范是严格按照‘圣经式的’,那我会有点担心。”
哈佐尼回答:“你当然会担心,因为我要求你做的是,愿意考虑最佳方案以外的可能性,比如,让基督徒在基督教地区管理一个基督教社会。”
他后来妥协了自己的立场: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这应该成为保守派加入新联盟的试金石。
作为新右派的统一主题,在课堂进行圣经教育是个小规模且具体的计划。但正如未来几周所证明的那样,对公共宗教的具体例子的关注是有先见之明的,并有助于为右派的一些最具争议的计划制定务实的路线。小组成员简短地考虑了这一提议,然后同意了,举杯庆祝。
2019年举行的第一届NatCon会议部分受到了哈佐尼《民族主义的美德》一书的启发,这本书是过去三年出版的右翼学术著作库中的一部,其它著作还包括帕特里克·迪内恩(Patrick Deneen)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和R.R.雷诺(R.R. Reno)的《强大上帝的回归》,这些作品阐述了作者眼中的美国问题的根源。
这个新的“后自由主义者”流派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过于关注,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建立了多元文化,传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却没有社会支持,同时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觉醒的”文化霸权。
他们将其中的许多弊端追溯到二战后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目标是通过在人权和多元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防止1940年代的恐怖卷土重来。雷诺认为,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了帮助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国王和国家传统主义的“强神”,代之以无尽的、兼具压迫性和开放性的“弱神”。
哈佐尼同意,战后的美国正确地处理了种族隔离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平等,黑人应该与白人平等,男人应该与女人平等,外国人应该与美国公民平等……已婚者与未婚者,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等等”,这就走得太远了,由此产生的政府应在文化上保持中立的观念导致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这是错误的“道路”。
在最高法院禁止课堂开设宗教课程仅仅两代人之后,“空洞、空洞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正如哈佐尼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人们无法区分男人和女人”。这种状况不仅激怒了那些不赞成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使他们的生活和支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遭到了攻击。
正如迪内恩(他是哈佐尼以前在罗格斯大学的同学,现在他是圣母院的政治学教授)最近写道:“自由主义的内部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原本负责培养人类美德的机构被废止,比如家庭、崇高的友谊、社区、大学、政体、教堂等”。
他认为,光靠保守派在私人生活中自修这些美德是不够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蹂躏证明了这一点。在废除“蓝色法律”(蓝色法律是指在特定日子限制或禁止某些活动的法律)之后,雇主现在可以自由地每周七天压榨他们的工人;由于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海外;而左派的“文化放松管制”意味着人们减少结婚,放弃宗教,生育的孩子也减少了。
后自由主义试图修正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它希望把民族主义从二战中恢复过来。正如哈佐尼在伯克基金会的同事安娜·威利斯告诉我的那样,真正的民族主义不属于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俄罗斯(这种民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更为准确),而是属于像威利斯的祖国波兰这样的国家,它们抵抗了这些国家。
在这种观点中,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排外,不如说是“自由地爱着属于自己的东西”。相比之下,许多聚集在NatCon的人认为今天的帝国主义者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利用企业的力量和国际契约来促进全球文化和法律秩序,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
保守的后自由主义者还指责说,公共中立的概念并不促进公平,反而会导致对大多数人的压迫,以及不可避免地滑向“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由此可见,如果政府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公平,反而总是在推进或破坏公共利益,那么法律就应该利用它的强制力来灌输美德。
这就是“整体主义”(integralism)的要旨,这是一个由许多杰出的后自由主义者推动的保守的天主教法律运动,它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将个人权利置于维护“共同利益”的体系之上。
在202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概述整体主义愿景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和前最高法院书记员阿德里安·维米尔(Adrian Vermeule)解释说:“与法律自由主义不同,公益宪政并导致政治统治和等级制度的恐怖,因为它认为法律像父母一样,是明智的老师,是良好习惯的灌输者。”
维米尔拒绝提供“具体细节”,说明违背人民自行决定‘什么对自己最好’的权力的实际意义,但表示,在整体主义下,围绕“言论自由、堕胎、性自由和相关事项”的法律将发生变化,首先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计划生育诉凯西”案中(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提出的个人有权定义自己对生命的意义的”可恶”主张。
维米尔补充说:“对传统的保守派来说,不能拒绝接种疫苗、自由主义的财产权和经济权等概念也将被抛弃”,这一立场在阿玛里最近对罢工的家乐氏公司工人的支持以及一位劳工领袖出席全国大会时得到了反映。
如果不是阿玛里2019年在《第一事件》(First Things)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这种理念可能还只是小众的学术活动。一篇是《反对死亡共识 》的团体宣言,宣布60年来存在的“共识保守主义”已经过时。另一篇是由推特风暴变成的文章《反对大卫·弗伦奇主义》,其中引用了从不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律师、评论员大卫·弗伦奇来嘲笑一种观点,即保守派可以按照自由主义的规则在文化战争中获胜。
相反,阿玛里坚持认为,他们必须“以击败敌人为目标,改变舆论,重新定位公共利益,以实现共同利益和最终的最高利益”。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口号,两年后在NatCon会议上仍被引用。随之而来的后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变得如此热烈,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粉丝艺术:去年11月,一张经过修改的《豪勇七蛟龙》电影海报在推特上疯传,描绘了“后自由主义七人组”:阿玛里、维米尔和迪内恩身穿狂野西部装束。标语是:“有时,共同的利益需要不寻常的人”。
![图片[1]-为了统一美国支离破碎的保守主义阵营,右翼先锋为何要去匈牙利和波兰寻找灵感-人文百科](https://www.caus.money/wp-content/uploads/2022/01/5GWxfSAwO4wPmEBS.jpg)
去年秋天,由于美国右派与匈牙利和波兰的统治阶级之间日益公开的联盟,整体主义再次受到关注,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将传统主义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这两个国家近年来已经具有了保守主义乌托邦的光环。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将保守的天主教与爱国主义相提并论,以至于最近波兰议会内供奉了两件天主教遗物,法律与正义党的竞选海报也在教堂内张贴。
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的政府已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明显“不自由”的基督教民主国家。它资助了一套广泛的估计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终身免征所得税),以防止穆斯林移民不能被同化,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只是一种幻觉”,并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儿童都应“按照基于匈牙利宪法身份和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来抚养。
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匈牙利,都不遗余力地争取美国保守派的支持。设在布达佩斯的私立学院马赛厄斯·科维努斯学院(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MCC),在过去两年里接待了被国内自由主义风气排挤的美国思想家。
10月,一个新的波兰对应机构Collegium Intermarium邀请了几位美国“政治天主教徒”,包括维米尔、阿玛里和《美国伟大》杂志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目前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的访问学者)格兰登·帕平(Gladden Pappin)举行“取消文化”会议(取消文化是一种社群抵制行为,由于某人或某节目的内容不符合自己认同的政治正确,发动网暴将其驱逐出网络甚至现实社交圈的活动)。
2021年6月,当这三个人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青年整体主义会议上发言时,匈牙利派了两位大使参加(其中一位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哈布斯堡后裔,是当今君主主义右派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东欧城市现在是后自由主义作家的重要图书推介站,欧尔班本人也鼓励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等美国保守派作家将匈牙利视为他们的“知识家园”。
这种积极拉拢已经得到了回报。德雷尔与MCC的联系以及他在布达佩斯另一个保守智库的住所,促使他在去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匈牙利最独裁的措施进行了越来越有力的辩护。
德雷尔总结说,欧尔班的“非自由的右翼倡议”,如禁止大学的性别研究课程,是抵制“左翼非自由主义”的必要措施。7月,俄亥俄州作家詹姆斯·戴维·万斯对欧尔班的生育政策大加赞赏,他甚至呼吁建立一个两级投票制度,使有子女的美国人比“无子女左派”拥有更多的选票。
8月,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记者)在布达佩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报道,将对欧尔班的采访在黄金时段播放到数百万福克斯观众的家中。而就在本周,特朗普宣布对欧尔班的“完全肯定并支持其连任总理”。
对这个新兴的右翼国际组织的报道也强调了整体主义的先锋领导人。到11月下旬,一个名为Substack的新运动,即后自由主义秩序启动的时候,整体主义甚至在电视节目《继承》中被简短提及。但突然崛起的声望也激发了天主教和学术界的批判。
2019年《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崛起》一书的进步作者马特·麦克马努斯认为:“天主教后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弱点是,尽管有了天主教的前缀,但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内心都是反动派。”
这本书描述了右派堕入自己的身份政治(即呼吁“重新确立某些曾一度占据主要地位的身份群体的权威)。
![图片[2]-为了统一美国支离破碎的保守主义阵营,右翼先锋为何要去匈牙利和波兰寻找灵感-人文百科](https://www.caus.money/wp-content/uploads/2022/01/O4coffV2HKS1Qw4H.jpg)
麦克马努斯在《偏见》(The Bias Magazine,宣扬基督教左翼的声音和观点)杂志上写道:“他们不仅要保护自由主义的成就,而且还想要超越这些成就,他们想让时钟倒流到前自由主义时代,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按照神圣的等级制度对个人进行分类,国家毫不犹豫地对非异性恋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采取惩罚措施”。
蒂莫西·特鲁特纳(Timothy Troutner)是圣母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为自由派天主教媒体《公益》(Commonweal)撰稿,在整体主义普遍采用之前的几年,他就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天主教徒的圈子里接触到了整体主义的雏形,他们普遍希望自己的信仰能反映到他们的政治承诺中。当这个群体最终分裂为“左派天主教徒”和整体主义者时,特鲁特纳看到后者的阵营转向丑陋:主张“中世纪的一些残酷的东西”,以及天主教右派的权力政治,专注于胜利和“击败敌人”。
在保守派中,也有大量整体主义的批评者。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汉比(Michael Hanby)认为,如果美国还存在,整体主义就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实现。
圣母玛利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战时20世纪最初的整体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而它的当代追随者,如网上论坛的评论者,他们欢呼“真正的圣徒公社”,“烧死异教徒”,“抓住犹太孩子”,强行转变他们的信仰,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效仿法西斯了。
最后,他写道,整体主义“是一种网络美学,主要参与者是被公共生活疏远、被统治欲支配的年轻人”,即权力意志。更多的主流保守派声音,如布雷特·斯蒂芬斯,干脆称其为神权主义。
尽管德雷尔在2017年出版的《本尼迪克特的选择》(The Benedict Option)一书被认为是当今后自由主义的先驱(在书中,他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包含了基督教灭亡的种子”),但去年秋天他开始呼应这些早期的批评。
他最近在《美国保守派》上写道,对整体主义的模糊定义可能听起来不错,但“当你开始问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时,它就会变得很奇怪”。
德雷尔广泛引用了一本由一位僧侣和一位神学家写的晦涩的2020年整体主义书籍,他想知道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否也在寻求一个只有受洗的天主教徒才能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非天主教的孩子可能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有限的例外,没有任何宗教少数群体的信仰自由可以得到保障。
整体主义者可笑地高估了会支持他们的天主教徒,德雷尔想象他们的人数,可能也就够塞满维米尔在剑桥的后院,而且“如果大多数人知道他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尖叫着跑开”。
这些批评引起了其他集体主义者的反击。迪内恩说,德雷尔可能是大卫·弗伦奇主义的新面孔;阿玛里说,德雷尔的后自由主义主要是“匈牙利类型的”。马可·鲁比奥的幕僚长迈克尔·尼德姆认为,整体主义者这样的“外部知识分子”,已经通过“移动奥弗顿之窗”(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理论)取得了一些成就。
维米尔写道,德雷尔缺乏政治想象力,看不到一小部分核心的坚定信徒能做什么。他引用法国反动知识分子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话说:“四五个人就能给法国带来一个国王”。而集体主义有后自由主义七人组。
如果这些派别内部的相互争执,在自由主义者的耳朵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它们大多确实是没有区别。毕竟,德雷尔、迪内恩和阿玛里都在《第一事件》中签署了2019年的“死亡共识”宣言。
当德雷尔呼吁他的后自由主义者同伴们,把整体主义的“思想实验”放在一边,而选择匈牙利更现实的模式时,他说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已经付出代价的政权。尽管11月的内斗很激烈,但在会议上和会后,欧尔班的匈牙利成了他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正如哈佐尼告诉我的那样,在NatCon会议上讨论的许多想法都很新,推动这些想法的人也“在行动”中。但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周内,他观察到了两个重要的整体主义转变:一个是对民族主义更全面的拥抱,一个是目标被扩大了,从一个以“最高利益”为命令的政权到对“普世整体主义”的柔和呼吁,正如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查德·派克诺德(Chad Pecknold)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
![图片[3]-为了统一美国支离破碎的保守主义阵营,右翼先锋为何要去匈牙利和波兰寻找灵感-人文百科](https://www.caus.money/wp-content/uploads/2022/01/kdKEKtbyIwUF0Pgv.jpg)
这种转变的主要例子是11月在《美国保守派》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由派克诺德、阿玛里和帕平共同撰写。这篇题为 《为文化基督教辩护 》的文章以四个场景开始:非婚同居的意大利前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政治集会上转动着祷告的念珠;离婚的法国前政治家玛丽安·勒庞(Marian Maréchal Le Pen)宣布基督教是法国身份的基石;不懂圣经的特朗普在谴责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照片中挥舞着圣经;以及欧尔班用公共资金在这个世俗的国家修复教堂。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些伪善的例子都没有问题,相反,它们是值得称赞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基督教秩序,”并不保证每个灵魂都能得到救赎,但宗教能够奠定结构。
“这四位领导人可能是坏的基督徒,但他们对基督教象征主义的信奉”,正如另一位NatCon演讲者所说的“宗教性氛围”,可能会进一步确立整体主义者想要的文化。毕竟,如果“清醒的意识形态”能够征服舆论,尽管“其真正的信徒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那么文化基督教可能也能做到这一点,从而“拯救并拥抱它的国家”。
对哈佐尼来说,这个论点展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实用主义,类似于他自己的会议提案,他也于去年秋天在匈牙利的MCC重复了这一提案。美国保守派的文章并不要求公众改变信仰,而是通过斡旋达成协议,即基督教应该在公共场所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那些人根本谈不上虔诚。
文章还重申了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之间的誓言,因为作者选择的所有四个“文化基督徒”的例子也都是明显的民族主义者。这是新保守派融合主义的基石。
伯克利大学宗教、和平和世界事务中心的研究员杰罗姆·科普斯基(Jerome Copulsky)说:“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就是保守派运动自1940年代和50年代以来的运作方式。“保守主义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如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南方农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冷战者,但当他们面对自由主义这个共同的野兽时,它们你要找到彼此相同的思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
今天的许多右翼的权宜之计是在争斗不休的派别之间谈判类似的休战:比如进行微小的差异调整,如迪内恩和·阿玛里不再自称自己是整体主义者,到关于如何将天主教的普遍性主张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等更大的调整。
阿玛里告诉我,虽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可以采取完全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会以一种“狭窄的、战术性的”方式支持“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好的,“因为它反对乌托邦式的无国界世界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实践中会导致普遍的暴政”,将人们沦为“零工工人”并威胁到传统信仰。
民族主义可以制衡这些弊端,而文化基督教可以提供帮助。他解释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基督教是这种无法被消灭的结构。随着自由主义的衰落,这种结构可以帮助西方国家重新连接到他们最深的根源,并促使道德更新,甚至是那些不具备深刻精神信仰的人群中”。
![图片[4]-为了统一美国支离破碎的保守主义阵营,右翼先锋为何要去匈牙利和波兰寻找灵感-人文百科](https://www.caus.money/wp-content/uploads/2022/01/clluwORCv4qgNIDZ.jpg)
缺乏信仰是对如今的美国的公平描述,在盖洛普民意调查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信仰的人不足总人口的一半。这也适用于波兰,那里的年轻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天主教(许多人认为它被政治化了),而在匈牙利,只有12%到15%的人口经常去教堂。
在这一点上,中欧不仅为文化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模式,而且对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提出了警告。在匈牙利,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信仰,这一现实导致欧尔班的支持者争辩说,“在欧洲,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 这似乎是一种迂回的方式,承认欧尔班最致力于维护的“基督教”,是以民族主义而非宗教术语来定义的。
这种批评甚至在国家保守主义的队伍中也被提到。2020年,在NatCon大会上发言的英国作家玛丽·哈灵顿(Mary Harrington)将“文化基督教”贬低为。不过是麦克马努斯诊断为后现代保守主义的 “空洞政治身份”。
哈灵顿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欧尔班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和它的许多民粹主义发现他们最令人信服的成绩不是在宗教教义或遵守中,而是在他们对局外人的定义中。如果‘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那唯一不被定义成基督徒的就是,外国人。”
虽然自由派的《公益》杂志上的作家特鲁特纳怀疑“文化基督教”是否有意作为种族代码,种族主义往往是文化基督教的后果。他说:“民粹主义言论的部分力量来自于,‘他们正在夺走你过去拥有的文化’。而任何吸引人们对社会变化不满的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包括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绪,如果你想让这种言论变得强大,你就得好好利用它。”
在NatCon会议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一些对公共基督教的呼吁没有美国保守党的文章那么有活力,似乎证明了这种趋势。前Newsmax评论员易木瑞·罗宾逊(Emerald Robinson)在推特上说,她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希望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极右翼挑衅者雅各布·沃尔在Gab上发帖说,应该要求所有美国犹太人都挂上圣诞灯,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叫同化)。而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吸引了许多QAnon信徒的大型教会会议上,失宠的迈克尔·弗林将军宣称:“如果我们要在上帝之下建立一个国家,那我们必须有一个宗教。”(一度有消息指弗林将是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但特朗普最终选择印第安纳州长迈克·彭斯出任他的副总统参选人)
当我就这些例子问哈佐尼,他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族群保持外人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根本现实。”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群体“应该庆幸没有像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那样受到迫害。我认为人们应该理解,多数和少数派不会实现完全的平等。 如果有人觉得,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应有的感激之情就是不体面的,或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和不公平,我就只能对他们说,他们对政治和人类社会的看法过于天真。”
他更尖锐地补充说:“所有这些推翻传统英美法律、宗教和语言的努力,正迫使人们在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后者在美国右派的边缘地带肯定会越来越强大。很多人有意识地将民族保守主义的复兴视为一种选择,试图阻止我们在极右翼看到的怪诞的政治冲动。”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最后通牒。正如雷诺在他的书中所论证的,“民族和文化忠诚的‘强神’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回归”。如果不欢迎他们以“我们最好的传统”形式回来,他们就会以“更黑暗的神的形式到来,而我们的开放社会正在阻止他们回来”。
这句话在NatCon会议上得到了回应,布朗大学教授格伦·卢利警告说:“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坚持用大写字母B拼写黑人,而把白人放在小写字母里的人(这里的白人指的是单词白色)”,或者那些把警察杀人事件政治化为“种族性死亡”的人是在“玩火”,只会诱发白人的逆反情绪。
阿玛里更直白地对我说,“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合理的国家理念,用基督教来调和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和野蛮的民族偶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我们的国家只会越来越混乱。”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似乎越来越小。去年整个春天,德雷尔在匈牙利的文章显示,他对欧尔班保护基督教文化的方法越来越欣赏。在一篇题为《维克多·欧尔班是对的》的文章中,他警告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在保持其对多元民主的承诺和其民族传统之间做出一个可怕的选择。
德雷尔在NatCon会议上说,在法国,“每个人都在担心与郊区的伊斯兰少数民族发生内战”,因此必须很快决定“要么停止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要么停止成为法国人。”
去年12月,他更进一步。
法国极右翼记者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曾两次被判煽动种族仇恨罪,他在一段视频中宣布竞选总统,视频中出现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以及街头暴力、蒙面妇女和穆斯林男子祈祷的画面。泽穆尔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犹太人,去年1月因“反人类罪”(实质上是大屠杀修正主义)受审,去年11月因煽动种族仇恨再次受审,他发誓要把法国“从压迫多数人的少数人手中夺回来”,这引起了“大替换”理论。
在推特上,阿玛里呼吁:“谁能用美国的语言,为美国人阐明泽穆尔的信息?”
第二天,德雷尔用美国的主题和美国本土的怨恨改写了泽穆尔的演讲。
与此同时,在波兰,去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成功地超越了前几年关于法西斯口号的报道,一群人烧毁了一份13世纪给予犹太人在波兰生活的合法许可文件,同时高呼“拒绝波林”,“波林”即波兰的希伯来语发音,还有“犹太人去死”的口号。
那一周,我与NatCon的组织者安娜·威利斯交谈。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一事件,但坚持认为她“这不可能是真的”。她觉得这是“故作聪明”,真相是俄罗斯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面临难民危机时,为抹黑波兰而进行的挑衅。但更重要的是,它“听起来不像她成长的国家”,在那里,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她的父亲和她的祖辈因抵抗共产党和纳粹而被捕,她相信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种族纯洁,而是任何人都能加入的忠诚契约。
几天后,威利斯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后来得知,令她沮丧的是,这一事件确实发生过。但她仍然努力想弄明白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她说,那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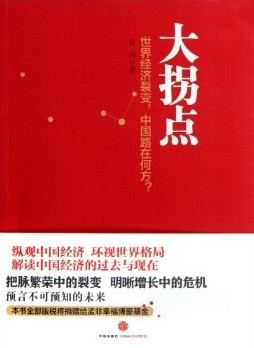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