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Baudrillard(1929 年 7 月 – 2007 年 3 月 6 日)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对文化研究感兴趣. 他以对媒体、当代文化和技术传播的分析以及对超现实等概念的阐述而闻名。鲍德里亚写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消费主义、经济批判、社会历史、美学、西方外交政策和流行文化。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诱惑》 (1978)、《拟像与模拟》 (1981)、《美国》 (1986) 和《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1991)。他的作品经常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尽管如此,鲍德里亚也反对后结构主义。并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
![图片[1]-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人文百科](https://www.rwp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23/03/image-24.png)
传记
鲍德里亚于 1929 年 7 月 27 日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兰斯。他的祖父母是农场工人,父亲是宪兵。高中期间,他通过哲学教授伊曼纽尔·佩莱特 Emmanuel Peillet 了解到超形上学pataphysics,据说这对理解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至关重要。当他搬到巴黎上索邦大学时,他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那里,他学习了德语语言和文学,这促使他从 1960 年到 1966 年开始在巴黎和外省的几所不同的中学教授这门学科。
教师生涯
在教学期间,鲍德里亚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并翻译了彼得·魏斯、贝尔托·布莱希特、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威廉·埃米尔·缪尔曼等作家的作品。
在教授德语的同时,鲍德里亚开始转向社会学,最终在亨利·勒斐伏尔、罗兰·巴特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论文委员会的指导下,于 1968 年完成并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Le Système des Objets(对象系统) 。随后,他开始在Paris X Nanterre教授社会学,这是一所位于巴黎郊外的大学校园,该校区在1968 年 5 月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鲍德里亚与哲学家汉弗莱·德·巴腾堡密切合作,后者将鲍德里亚描述为“有远见的人”。在南泰尔,他先后担任Maître Assistant(助理教授)和Maître de Conférences(副教授),最终在完成L’Autre par lui-même(The Other by Himself)认证后成为教授。
1970 年,鲍德里亚第一次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1973 年多次前往日本京都。他于 1981 年在日本获得了第一台相机,这使他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1986 年,他转到巴黎第九大学的IRIS(研究与信息社会经济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formation Socio-Économique) ,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后期教学生涯。在此期间,他开始远离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尤其是其“经典”形式),并且在停止全职教学后,他很少将自己与任何特定学科联系起来,尽管他仍然与学术界保持联系。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他的书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名人,经常在讲法语和英语的大众媒体上发表。尽管如此,他仍继续支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创新研究所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Innovation Sociale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并且是Pataphysique学院的总督satrp。鲍德里亚在瑞士萨斯费的欧洲研究生院任教,并与加拿大理论、文化和技术评论Ctheory合作,在那里他被大量引用。据称,从 2004 年创刊到他去世,他还参与了国际鲍德里亚研究杂志。
1999 年至 2000 年,他的照片在巴黎的 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展出。 2004年,鲍德里亚参加了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举办的关于他的作品“鲍德里亚与艺术”的大型会议。
个人生活
鲍德里亚喜欢巴洛克音乐。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 (Claudio Monteverdi)。他还偏爱摇滚乐,例如The Velvet Underground 和 Nico。
鲍德里亚使用“他的旧打字机,从不使用电脑”来写作。他曾表示,计算机“不仅仅是一种更方便、更复杂的打字机”,而对于打字机,他有“与写作的物理关系”。[59]
鲍德里亚结过两次婚。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露西尔鲍德里亚有两个孩子,吉尔斯和安妮。
1970 年,鲍德里亚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遇到了 25 岁的玛丽娜·杜普伊斯 (Marine Dupuis),当时她来到他担任教授的南泰尔大学。Marine 后来担任媒体艺术总监。他们于 1994 年结婚,当时他 65 岁。
鲍德里亚于 2005 年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在巴黎圣伯夫街的公寓里与疾病抗争了两年,享年 77 岁。Marine Baudrillard 策划了 Cool Memories,这是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的朋友协会。
关键概念
鲍德里亚的出版作品成为一代法国思想家的一部分,包括:吉尔·德勒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和雅克·拉康,他们都对符号学感兴趣,他经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哲学学派的一部分。
詹姆斯·M·罗素James M. Russell 在 2015年指出,“鲍德里亚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论点始终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意义和意义都只能根据特定单词或“符号”如何相互关联来理解。鲍德里亚认为,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意义是通过符号系统共同作用来实现的。继结构主义 语言学家 费迪南德·索绪尔之后,鲍德里亚认为意义(价值)是通过差异创造的——通过某些东西不是(所以“狗”的意思是“狗”,因为它不是-“猫”,不是-“山羊”,不是-“树”等)。事实上,他认为意义已经足够接近自我指涉:物体、物体的图像、文字和符号位于意义之网中;一个对象的意义只能通过它与其他对象的意义的关系来理解;例如,一件事的声望与另一件事的平凡有关。
从这个起点出发,鲍德里亚根据这种自我指涉性对人类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他的作品描绘了社会总是在寻找一种意义感——或对世界的“全面”理解——但始终难以捉摸。与后结构主义(例如米歇尔·福柯)相反,对后结构主义来说,知识的形成只是权力关系的结果,鲍德里亚发展了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对全面知识的过度、徒劳的探索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错觉。在鲍德里亚看来,(人类)主体可能试图理解(非人类)客体,但是因为客体只能根据它所指的来理解(并且因为意指过程直接涉及其他符号的网络,从中它是有区别的)这永远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主题更确切地说是被诱惑(在拉丁语的原始意义上:seducere, ‘带走’) 宾语。因此,他认为,归根结底,完全理解人类生活的细节是不可能的,当人们被引诱去思考其他方面时,他们就会被吸引到现实的“模拟”版本中,或者使用他的一个新词,一种“超现实”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世界变得不真实,而是说社会越快、越全面地开始将现实整合成一幅据称连贯的图景,它看起来就越不安全和不稳定,社会就会变得越可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消亡了”。
罗素指出,鲍德里亚认为,“在我们当前的‘全球化’社会中,技术交流造成了意义的过度扩散。正因为如此,意义的自我指涉性催生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个意义被剥夺的世界。 ” 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 20 世纪晚期的“全球”社会中,过多的符号和意义导致了(相当矛盾的)现实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都不再被相信。我们生活,他争辩说,不是在一个“地球村”,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的短语,而是在一个即使是最小的事件也更容易石化的世界中。因为“全球”世界在符号和商品交换的层面上运作,它变得越来越无视象征性的行为,例如恐怖主义。在鲍德里亚的作品中,象征领域(他通过马塞尔·莫斯和乔治·巴塔耶的人类学著作发展了一种观点)被视为与符号和意义截然不同的领域。标志可以像商品一样交换;另一方面,符号的作用完全不同:它们像礼物一样被交换,有时作为夸富宴的一种形式猛烈地交换. 鲍德里亚,尤其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认为“全球”社会没有这种“象征性”元素,因此象征性地(如果不是军事上)无法抵御拉什迪法特瓦或实际上是9 月 11 日恐怖袭击等行为反对美国及其军事和经济机构。
对象价值系统
在他的早期著作,如《对象系统》、《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的主要关注点是消费主义,以及不同对象如何以不同方式消费。此时,鲍德里亚的政治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和情境主义)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些书中,他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卡尔·马克思不同。对于鲍德里亚和情境主义者而言,消费而非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驱动力。
鲍德里亚是通过批判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得出这一结论的。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太容易和太简单地接受了真正需要与真正使用相关的观念。鲍德里亚借鉴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观点,认为需求是建构的,而不是天生的。他强调,所有的购买,因为它们总是在社会上具有某种意义,所以都有其拜物教的一面。对象总是从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那里汲取灵感,对它们的用户“说些什么”。对他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过去并且仍然比生产更重要的原因:因为“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他写道,一个对象有四种获取价值的方式。四个价值创造过程是:
功能价值:一个对象的工具性目的(使用价值)。例子:一支笔写;冰箱冷却。
交换价值:一个物体的经济价值。示例:一支钢笔可能抵得上三支铅笔,而一台冰箱可能抵得上三个月工作的工资。
象征性价值:一个客体相对于另一个主体(即在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赋予的价值。例如:一支笔可能象征着学生的毕业礼物或毕业典礼演讲者的礼物;或者钻石可能是公开宣布的婚姻爱情的象征。
符号值:一个对象在对象系统中的值。示例:一支特定的笔虽然没有额外的功能优势,但相对于另一支笔可能具有声望;钻石戒指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功能,但可能暗示特定的社会价值,例如品位或阶级。
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试图论证这些价值观中的前两个不是简单地相关联,而是被第三个,尤其是第四个所打断。后来,鲍德里亚彻底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生产与象征交换与死亡之镜》)但直到他去世,他的工作仍然关注符号价值(与商品交换有关)和象征价值(与莫斯礼物交换有关)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它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他关于世界大事的著作中。
拟像Simulacra 和模拟
随着鲍德里亚在整个1980年代的发展,他从经济理论转向调解和大众传播。尽管保留了对索绪尔 符号学和符号交换逻辑(受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影响)的兴趣,鲍德里亚将注意力转向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作品,发展了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如何由交流形式决定的思想一个社会雇用。通过这样做,鲍德里亚超越了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形式符号学来考虑历史上理解的结构符号学版本的含义。根据 Kornelije Kvas 的说法,“鲍德里亚反对不同形式的语言组织等价的结构主义原则,即包含对立的二元原则,例如:真-假、真实-不真实、中心-边缘。他否认任何(模仿)的可能性) 现实的复制;通过语言中介的现实变成了符号游戏。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真实与虚构、副本与原件之间的所有区别都消失了”。
鲍德里亚声称,模拟是拟像的当前阶段:一切都由没有指涉对象的参考组成,是一种超现实。-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拟像以仿制品的形式出现,其中人或物似乎代表不存在的真实指称(例如,皇室、贵族、圣洁等)。随着工业革命,占主导地位的拟像成为产品,可以在无穷无尽的生产线上繁殖。在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拟像是模型,它本质上已经代表着无限的可复制性,并且它本身已经被复制了。
历史和意义的终结
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鲍德里亚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是历史性,或者更具体地说,当今社会如何在其政治选择中使用进步和现代性的概念。他与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很像,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历史已经结束或“消失” ;但是,与福山不同的是,鲍德里亚断言,这一结局不应被理解为历史进步的顶点,
这种世界秩序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终结,不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以民主实现为基础,而是以预防性恐怖为基础,以反恐为基础结束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
— 鲍德里亚,《邪恶的智慧》或《清醒契约》。纽约:Berg Publishing,2005,Chris Turner
但作为历史进步的理念的崩溃。对鲍德里亚来说,冷战的结束并不代表意识形态的胜利;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右翼和左翼之间共同的乌托邦愿景的消失。鲍德里亚进一步证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共产主义愿景和自由主义的全球公民社会愿景,他争辩说,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一直是幻想;事实上,正如终结的幻觉所言,他认为终结的想法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梦想:
唉,历史的终结也是历史垃圾箱的终结。不再有任何垃圾箱可以处理旧的意识形态、旧的制度、旧的价值观。我们要把创造历史垃圾箱的马克思主义扔到哪里去?(然而,这里有一些正义因为发明它们的人已经陷入了困境。) 结论:如果历史不再有垃圾箱,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垃圾箱。它已经成为自己的垃圾箱,就像地球本身正在成为自己的垃圾箱一样。
他认为,在一个受快节奏电子通信和全球信息网络支配和统治的社会中,这种门面的崩溃总是不可避免的。鲍德里亚使用引起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愤怒的准科学词汇,写道社会发展的速度破坏了历史的线性:“我们拥有粒子加速器,它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事物的参考轨道。 “ [
罗素表示,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表明鲍德里亚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有密切关系”,利奥塔认为在 20 世纪末,“元叙事”不再有任何空间。(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是这样一种元叙事。)但是,除了简单地哀叹历史的崩溃之外,鲍德里亚还超越了利奥塔,试图分析积极进步的想法是如何在有效性下降的情况下被采用的. 鲍德里亚认为,虽然真正相信历史有一个普遍的终点,即所有冲突都会找到解决办法,这被认为是多余的,但普遍性仍然是世界政治中用作行动借口的概念。在他看来,没有人再相信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曾经并且仍然被夸夸其谈地用来为其他不合理的选择辩护。他写道,即使目的不再被相信,手段仍然存在,手段被用来隐藏当下的严酷现实(或者,用他的话说,不真实)。“在启蒙运动中,普遍化被视为无限增长和向前进步。相比之下,今天,普遍化被表达为向前逃避。” 这涉及“末日幻觉”中概述的“逃逸速度”的概念,这反过来又导致逃逸速度的后现代谬误,根据定义,后现代思想和批判观点不能真正摆脱包罗万象的“自我指涉”话语领域。
政治评论
关于波斯尼亚战争
鲍德里亚在著作中回应了西方对波斯尼亚战争的冷漠,主要是在他的解放专栏中的文章中。更具体地说,他表达了他对欧洲不愿回应“波斯尼亚的侵略和种族灭绝”的看法,其中“新欧洲”暴露了自己是一个“骗子”。他批评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从事无效、虚伪和自私的行动,批评公众无法区分拟像与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其中真正的死亡和破坏在波斯尼亚似乎不真实。他决心在他的专栏中公开指出肇事者,塞尔维亚人,并将他们在波斯尼亚的行为称为侵略和种族灭绝。
鲍德里亚“曾攻击苏珊桑塔格”,因为他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导演了一部戏剧。
关于波斯湾战争
鲍德里亚 1991 年的挑衅性著作《海湾战争没有发生》提升了他作为学术和政治评论员的公众形象。他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克劳塞维茨公式的反面:不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政治”,而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政治缺失”。因此,萨达姆·侯赛因并不是在与联军作战,而是用他士兵的生命作为一种牺牲形式来维护他的权力。 与 伊拉克军队作战的联军只是每天投下10,000吨炸弹,好像在向自己证明有敌人要打。 西方媒体也是同谋,实时呈现战争,通过重复使用战争图像来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和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正在战斗的观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案子。萨达姆侯赛因没有使用他的军事能力(伊拉克空军)。他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他轻松镇压了随后发生的1991 年内部起义就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变化不大。萨达姆没有被打败,“胜利者”没有胜利,所以没有战争——也就是没有发生海湾战争。
该书原为英国《卫报》和法国《解放报》的连载文章,分三部分出版:《海湾战争不会发生》,发表于美国军事和修辞集结期间;“海湾战争没有发生”,在军事行动期间出版;之后出版了《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一些批评家,如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指责鲍德里亚的即时修正主义;否认冲突的实际行动(这与他对一般现实的否认有关)。因此,鲍德里亚被指责为懒惰的非道德主义、愤世嫉俗的怀疑主义和贝克尔式 的主观唯心主义。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如威廉·梅林,在他的书《鲍德里亚与媒体》中, 认为鲍德里亚更关心西方的技术和政治主导地位及其商业利益的全球化,以及这对目前战争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梅林争辩说,鲍德里亚并没有否认发生了什么事,而只是质疑那件事实际上是战争还是双边“伪装成战争的暴行”。梅林认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指责是多余的,而且是基于误读。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来说:
萨达姆清算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与他更加调情;他向库尔德人放毒气,这不是对他不利的;他消灭了宗教干部,整个伊斯兰教与他和平相处……甚至……100,000 人的死亡将只是萨达姆牺牲的最后一个诱饵,根据计算的等价物没收的血钱……以保存他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这些死者还为那些不想白白兴奋的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至少这些死者将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一场战争,而不是可耻的和毫无意义的。
关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
在他的文章“恐怖主义精神”中,鲍德里亚将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袭击描述为“绝对事件”。鲍德里亚将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绝对事件”与“全球事件”进行对比,例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之死和世界杯。这篇文章的高潮是鲍德里亚将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件”,”或“没有发生的事件”。为了将它们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技术和政治扩张的反应,而不是一场基于宗教或文明的战争,他描述了绝对事件及其后果如下:
这不是文明或宗教的冲突,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伊斯兰教和美国,人们正在努力将冲突集中在这两个国家,以制造明显对抗和基于武力解决方案的错觉。这里确实存在根本的对立,但它指向美国的幽灵(它可能是全球化的中心,但绝不是全球化的唯一体现)和伊斯兰教的幽灵(它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化身)胜利的全球化与自身作斗争。
根据他的社会理论,鲍德里亚将这些袭击描述为对基于商品交换的世界不可阻挡的崛起的象征性反应。
与雅克·德里达辩论
2003 年 2 月 19 日,随着2003 年对伊拉克的入侵迫在眉睫,勒内·梅杰René Major 主持了一场题为“Pourquoi La Guerre Aujourd’hui?”的辩论。Baudrillard和 Jacques Derrida之间。辩论讨论了恐怖袭击与入侵之间的关系。俄克拉荷马大学文森特·雷奇教授指出,“鲍德里亚将 9/11 事件定位为伊拉克战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而“德里达则认为伊拉克战争早在 9/11 事件之前就已计划好,9/11 事件起着次要作用”。
权力的痛苦
2005 年,鲍德里亚写了三篇短文,并接受了一次简短的杂志采访,都表达了相似的想法;在他于 2007 年去世后,这四篇文章被收集起来并在他死后出版,名为《权力的痛苦》( The Agony of Power) ,这是一场反对权力本身的论战。第一篇文章“从统治到霸权”对比了它的两个主题,即权力模式;统治代表历史上传统的权力关系,而霸权代表现代的、国家和企业所实现的更复杂的权力关系。鲍德里亚谴责当代企业公开陈述其商业模式时所表现出的“冷嘲热讽” 。例如,他引用了法国电视频道TF1 的高管帕特里克·勒莱 (Patrick Le Lay) 的话表示,他的公司的工作是“帮助可口可乐销售其产品”。 鲍德里亚感叹这种诚实先发制人,从而剥夺了左派批评政府和企业的传统角色:“事实上,勒莱夺走了我们仅存的权力。他窃取了我们的谴责。”因此,鲍德里亚指出“权力本身必须被废除——不仅是拒绝被支配……而且,同样强烈地,是拒绝支配。”
后面的文章包括对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的进一步分析,使用美洲原住民夸富宴的比喻来描述美国和穆斯林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与劫机者的关系。在这些作品的上下文中,“夸富宴”不是指仪式的送礼方面,而是指破坏财富的方面:“恐怖分子对西方的夸富宴就是他们自己的死亡。我们的夸富宴是侮辱、不谦虚、淫秽,退化和卑鄙。” 这种对西方的批评带有鲍德里亚的拟像、上述商业犬儒主义以及穆斯林和西方社会之间的对比:
我们 [西方] 将这种冷漠和卑鄙当作一种挑战扔给其他人:挑战以玷污自己作为回报,否认他们的价值观,脱光衣服,坦白,承认——以回应与我们自己相同的虚无主义。
反响
洛特林格指出,“以慷慨着称”的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在鲍德里亚发表了对福柯作品的看法后,“让整个巴黎都知道”他认为鲍德里亚是“职业的耻辱”。
桑塔格在回应鲍德里亚关于她对波斯尼亚战争的反应的评论时,形容他是“无知和愤世嫉俗”和“政治白痴”。
詹姆斯·罗素 (James M. Russell) 在 2015 年写道,“最严厉的”鲍德里亚“批评者指责他是一种否认现实的非理性主义形式的传播者”。 鲍德里亚的编辑之一,批判理论教授马克·波斯特评论道:
鲍德里亚直到 80 年代中期的作品都受到了一些批评。他没有定义关键术语,例如代码;他的写作风格是夸张和陈述性的,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缺乏持续的、系统的分析;他总结了自己的见解,拒绝限定或界定他的主张。他写的是特定的经历、电视画面,仿佛社会上的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从那个有限的基础上推断出一个凄凉的世界观。他忽略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例如新媒体提供的许多好处。
但是 Poster 仍然主张他的当代意义。他还试图反驳对鲍德里亚最极端的批评:
鲍德里亚并不是在争论理性在某些行动中仍然有效的微不足道的问题,例如,如果我想到达下一个街区,我可以假设一个牛顿宇宙(常识),计划一个行动方案(直走X 米), 执行动作, 并最终通过到达所讨论的点来实现我的目标。值得怀疑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否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现在。在鲍德里亚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超现实主义通过媒体的同时传播以及作为主要叙事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崩溃,剥夺了理性主体获得真理的特权。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个人不再是公民,不再渴望最大化他们的公民权利,也不再是无产者,期待共产主义的到来。他们更像是消费者,因此是代码定义的对象的猎物。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 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超越》 ——试图分析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持续的、但不安的且很少明确的关系)以及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反驳。关于前者,William Merrin(上文已讨论)发表了不止一篇对 Norris 立场的谴责。后者鲍德里亚本人将其描述为还原性的。
凯尔纳表示,“很难决定鲍德里亚是作为科幻小说和超形上学,还是作为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形而上学来最好地阅读,以及他 70 年代后的作品应该以真实还是虚构的方式来阅读。” 对凯尔纳而言,鲍德里亚在 1970 年代及之后“沦为技术决定论和符号学唯心主义的牺牲品,它们假定了一种自主技术”。
凯尔纳评论说,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交换与死亡》中的观点是“极左”的。鲍德里亚后来承认,他的观点可以“客观地”归类为右翼,但发现左右政治光谱是武断的。
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塞尔 (Adrian Searle)于 1998 年将鲍德里亚的摄影描述为“充满渴望的、优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就像“未被关注时刻的电影剧照”。
语气和态度
马克·费舍尔指出,鲍德里亚“被谴责,有时被崇拜,作为一个已逝现实的忧郁观察者”,断言鲍德里亚“当然是忧郁的”。海报指出,“随着六十年代政治的消退,鲍德里亚的激进主义也随之消退:他从坚定的左派立场逐渐转向凄凉的宿命论”,菲利克斯·瓜塔里 Felix Guattari回应了这一观点。Richard G. Smith、David B. Clarke 和 Marcus A. Doel 反而认为鲍德里亚是“极端乐观主义者”。在批判理论家McKenzie Wark和 EGS 教授Geert Lovink的交流中, 沃克评论鲍德里亚,“他写的一切都带有极度悲伤的特征,但总是以最快乐的形式表达。” 鲍德里亚本人表示“我们必须与不真实、缺乏责任感、虚无主义和绝望的指控作斗争”。Chris Turner 对 Baudrillard’s Cool Memories: 1980–1985 的英译本写道:“我指责自己……极度肉欲和忧郁……阿门”。
大卫·梅西在鲍德里亚对福柯的看法中看到了“异常的傲慢”。 桑塔格认为鲍德里亚“居高临下”。
罗素写道:“鲍德里亚的作品,以及他不妥协的——甚至是傲慢的——立场,招致了激烈的批评,这在当代社会学术界只能与雅克·拉康所受到的批评相提并论。”
恐怖主义评论
鲍德里亚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的立场受到了两方面的批评。理查德·沃林(在《无理的诱惑》中)强烈指责鲍德里亚和斯拉沃热·齐泽克几乎是在庆祝恐怖袭击,基本上声称美国得到了它应得的。然而,齐泽克在《批判性调查》杂志上反驳了对沃林分析的指责,认为沃林的分析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野蛮行为,他说沃林没有看到幻想一个事件和说一个人应该得到那个事件之间的区别。梅林(在鲍德里亚和媒体中)认为鲍德里亚的立场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一种道德优势。在杂志上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梅林进一步指出,鲍德里亚赋予社会的象征性方面以高于符号学关注的不公平特权。其次,作者质疑攻击是否不可避免。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在《批判性调查》(Critical Inquiry)中指出,鲍德里亚认为,它们的毁灭是被创造它们的社会所迫,暗指双塔是“因自身重量而倒塌”的观点。在拉图尔看来,这是因为鲍德里亚只是从象征和符号二元论的角度来构想社会。
在流行文化中
沃卓斯基姐妹说,鲍德里亚影响了黑客帝国(1999),而尼奥则《拟像和模拟》中隐藏了包含信息的金钱和磁盘。但鲍德里亚本人否认与《黑客帝国》有任何联系,称这充其量是对他的想法的误读。
一些评论家指出,查理考夫曼的电影Synecdoche, New York似乎受到鲍德里亚的《拟像和模拟》 的启发。
摇滚乐队猎鹿人的专辑《为什么一切还没有消失?》受到鲍德里亚同名散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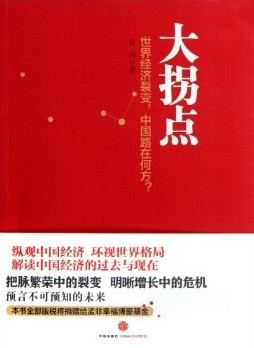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