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观念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其中,最富于成就的观念,就是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观念。农民起义、宗教改革没有这样的观念,是知识分子——科塞称为“观念人”——最早把它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知识分子萌生于中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壮大为一个有为的群体。在价值观的形成方面,他们是从社会底层、被压迫阶级哪里获取资源的,因此蕴含着不满和反抗,在本质上说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接受自己的出身,而以全民代表自许;这种公共的身份促使其致力于改变全局,为实现理想中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而斗争。
除了制造观念,知识分子还利用这些观念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从而导致他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并使他们的行动在政治过程中转趋激烈。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在观念形态和革命组织的系列技术性工作,要进行具有相当规模的、有效率的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西班牙哲学家约瑟·加塞特在《现代主旋律》中猜测说,革命“并非由各种堡垒组成,而是由人们的思维状态所构成”,因此,虽然促成革命的动力因素来自多个方面,知识分子“总是占据着革命舞台的中心”。法国人保罗·利科则说:“只要革命的动力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只要革命涉及到权力与真理以及与正义的关系,知识分子将被推到革命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仅仅参与革命。”他以上个世纪失败的匈牙利和成功的波兰革命为例,说明知识分子在反抗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托克维尔看来,知识分子的特长在于洞察力和想象力。他强调,要应付一个变化的世界,光凭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创新能力,是观念、远见和热情推动着人类事业的发展。他提醒说,特别在动荡和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关注是什么迷住了梦想家的想象力,比了解有经验的人所思考的东西更重要。”
托克维尔以法国革命为例说,其中那些与革命同步,对社会运动有洞察力的人,并非是富于管理经验的权力者,而是那些具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的文学之士。他承认,他们在摧毁旧制度方面表现十分激进,但不能容忍他们在革命中的“残暴性”,责备他们以浪漫的方式从事“必然性的破坏”。他解释说,他谴责的不是革命的基本原则,而是过激的行动,循此原则走得太远。他想要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政治文化,一种“中庸”行为,处方是大胆的政治想象力与有序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他注意到,革命在美国通向自由,在法国则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奴役状态;与法国的文学出身的革命家不同,美国的建国之父不仅有思想和知识,还有在政府部门内部及非暴力政治冲突中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
说到底,托克维尔是代议制的维护者。他的所谓“经验”,不免过于依赖旧日的积累;而突然而至的革命,面对紧迫而陌生的情势,许多政策和策略是无从借鉴的,只好依靠临时的创造。所以说,革命是一项伟大的政治试验;没有这种试验,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经验。
伏尔泰早已看到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联系。他说:“我看到的每件事都在为革命播下种子,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我是没有那么幸运能够见证它了。法国总是落在别人的后面,但最终他们还是到达了目的地。渐进的启蒙已经如此广泛地传播,以至于一有机会它就会爆发,而且接下来就会有一场巨大的混乱。年轻的一代是幸运的,他们将看到一些伟大的事情。”
知识分子总是走在革命的前面,他们是各种革命的催生者。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说,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用餐,要是那个晚上饭厅的天花板垮了下来,就不会有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这些看来并不务实的言词主义者在任何群众抗议运动或革命开始时都是不可缺少的,直到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甚至临近高潮时,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将军、工业家和士绅才参加进来。
但是,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往往不能深入。葛兰西批评说,他们陷于历史宿命论的神话之中,没有引导人民和民主运动,帮助发展中的力量,使之在具体行动中变得更积极、更有实干性。对于知识分子过分执着于自身的理性,他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铁的独裁。”
知识分子有必要唤起民众,特别是农民,建立联盟以壮大革命的力量。知识分子的革命能力,取决于他们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也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其他民众的支持。
日本哲学家和政治家中江笃介称法国大革命为一出大型戏剧,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是“剧作家”,西耶斯、米拉波、罗伯斯庇尔、丹东等革命者则是戏中的演员。他认为这出戏剧只有得到观众的支持才能上演,如果失去这种支持,最终将被强大的宫廷力量所粉碎。1873年到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党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有意唤起农民的自觉行动,结果努力失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鼓动农民参加游击战争,基本上也是以失败收场。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较大,不容易取得彼此之间的认同,加以来自政府方面的破坏,革命联盟往往建立不起来。
至于联盟的构成,并不意味着取消知识分子的特性,使之成为其他集团的附庸;反之更加突显其主导的地位,他们永远是革命的头脑和灵魂。
革命领袖来源于知识分子,又不同于知识分子。由于革命不同于造反,革命领袖必然体现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念,这是他们固有的知识分子性质。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仅限于提供知识、观念和理论,而革命领袖则致力于理论实践,制造对信仰的饥渴。他们原本是同科植物,权力使之变异。
霍弗在他的书中创造了一个“言辞人”(men of words)的角色,即我们惯称的知识分子。他说,这是群众运动中的真正的悲剧角色。
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劫持了运动,使之成为夺取权力宝座的工具。因此,有人认为,群众受其欺骗,误以为自由即将来临。霍弗指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在运动中唯一被欺骗的只有言辞人。他们最初站起来反抗旧制度,批判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各种专制政策,要求给予个人自由的权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响应他们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其实,群众所需要的并非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这种自主性,摆脱如陀思妥也夫斯基说的“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他们仅仅需要信仰,一种盲目的、独裁的信仰。他们推翻旧秩序,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统一体。霍弗说,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往往是群众渴求的结果,他们始终没有受骗。
霍弗揭示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不管他们怎样热情讴歌群众运动,都无法做到最终消融自我。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进那些根本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所以得势,正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
霍弗又把言辞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造力的,一种是没有创造力的。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不管如何批判旧秩序,到底是依恋“现在”的,他的激情在于改革而非摧毁。但是,这只是在群众运动尚未失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对旧制度的斗争进一步白热化,只有凭借坚强团结和自我牺牲才可望取胜时,这些有创造力的言辞人就会被推到一边,权力最终落入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手上,而他们乃是一群激烈反对“现在”的人。
有创造力的言辞人愈觉得自己跟一个激烈运动的气氛格格不入,时间一长,将无可避免地扮演起异端的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离世,不然,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
霍弗把马拉、罗伯斯庇尔、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一并划入后来蜕变为狂热者角色的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范围。这在理论上过于含混,混淆了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界限。事实上,无论革命领袖或是大独裁者,都不是没有创造力的人物。
在启蒙思想家中,只有孔多塞活着看到希望已久的革命的发生,但最后仍然要逃离恐怖统治,并于1794年死于狱中。
《百科全书》派人物,大约有十多位参与起草会议记录的地方议员,他们未曾表达过取消贵族或君主制的意愿,显然他们不是共和主义者,不满于革命的狂暴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但那结果一样不妙:其中一部分逃离巴黎,或者流亡国外;在恐怖时期有四个人被监禁,一个人被处死。
当革命处于高潮,它趋于信仰至上,意志统一,不容异议和反对。而知识分子偏偏喜欢质疑,结果为革命所淘汰。鲁迅多次提到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遭遇,并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也有婴儿。当然,也有没有婴儿而只有血和污秽的革命。
妃格念尔在法庭上讲道:
“在我所据以行动的纲领中,对我最有意义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消灭专制的统治方式。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实践意义。我想,不妨向往共和制。但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只有社会已作好准备的那种政体,因此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出现让人有可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来为社会造福创造条件。我认为,在我们现存的秩序下不存在这种条件。”
妃格念尔是一位反乌托邦主义者。她可能并不明确未来的新时代具体为何,但清楚地知道乃是现行制度的反面;因为唯现实是可把握,可实现的,所以,革命者只须反抗现行制度即完成新时代的准备工作。其实一代人的使命亦止于此。学者热衷于讨论问题:革命还是改良?暴力还是非暴力?正如妃格念尔清醒地意识到的这样:选择什么政体,采取什么行动,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意义”,在她看来,完全在于可实践性。否则,任何推理所得的结论都是荒谬的。
——摘自《革命寻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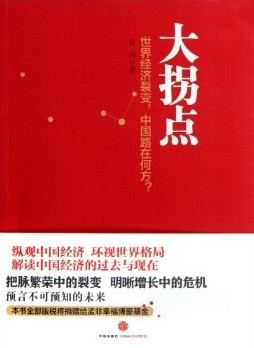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