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原名杰基·埃利·德里达;1930 年 7 月 15 日 – 2004 年 10 月 9 日)是一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他发展了解构哲学,他在许多文本中都使用了这种哲学,是通过仔细阅读费迪南德·索绪尔以及胡塞尔的语言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而发展起来的。他是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相关的主要人物之一,尽管他与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并且从未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词。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德里达出版了 40 多本书,以及数百篇论文和公开演讲。他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哲学、文学、法学、人类学、史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精神分析、 音乐、建筑和政治理论。
他的作品在整个美国、欧洲大陆、南美洲和所有其他大陆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保持着重要的学术影响,特别是在围绕本体论、认识论(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伦理学、美学、诠释学和语言哲学的辩论中,在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大部分盎格鲁圈子中,德里达的影响目前在文学研究中最为明显,由于他长期以来对语言的兴趣以及他在耶鲁大学期间与著名文学评论家的交往。他还影响了建筑(以解构主义的形式)、音乐(尤其是在幽灵学Hauntology的音乐氛围中)、艺术和艺术批评。
特别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德里达在他的作品中处理了伦理和政治主题。一些评论家认为《言语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 (1967) 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他包括:语法学Of Grammatology (1967)、写作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7) 和哲学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 (1972)。这些著作影响了各种活动家和政治运动。他成为了一位知名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而他的哲学方法和他的作品臭名昭著的深奥使他备受争议。他经常被提名,但从未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图片[1]-雅克·德里达-人文百科](https://www.rwp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23/03/image-7.png)
生活
德里达于 1930 年 7 月 15 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El Biar(阿尔及尔)的避暑别墅,父亲是海姆·亚伦·普罗斯珀·查尔斯(被称为“艾梅”)德里达,他一生都在葡萄酒和烈酒公司Tachet工作,包括担任旅行推销员(他的儿子反映这份工作“令人筋疲力尽”和“羞辱”,他的父亲被迫成为一名“温顺的员工”,以至于早起在餐厅做账目。他的母亲是西班牙裔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并于33年成为法国人,当时克雷米厄法令授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完全的法国公民身份。他的父母将他命名为“Jackie”,“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尽管当他搬到巴黎后,他后来采用了一个更“正确”的名字版本;一些报道表明,他以美国儿童演员杰基·库根 ( Jackie Coogan)的名字命名,杰基·库根 (Jackie Coogan) 因在 1921 年的查理·卓别林 ( Charlie Chaplin)电影中扮演的角色而闻名于世。在他割礼时,他的叔叔 Eugène Eliahou也给了他一个中间名Élie; 与他的兄弟姐妹不同,这个名字没有记录在他的出生证上,后来他将其称为他的”隐名”。
德里达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哥哥保罗·莫伊兹 (Paul Moïse) 在不到三个月大时就去世了,也就是德里达出生的前一年,这让他一生都在怀疑自己的角色是他已故哥哥的替代者。德里达在阿尔及尔和埃尔比阿尔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1942 年学年的第一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行政人员——执行维希政府设定的反犹太主义配额——将德里达开除出他的中学。他偷偷逃学一年,不愿去流离失所的师生组成的犹太中学,还参加了许多足球比赛(他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德里达在哲学家和作家(如卢梭、尼采和纪德)的作品中找到了反抗家庭和社会的工具。他的阅读还包括加缪和萨特。
1940 年代后期,他就读于阿尔及尔的Lycée Bugeaud,1949 年他移居巴黎,就读于Lycée Louis-le-Grand,他的哲学教授是艾蒂安·博恩Étienne Borne。那时他正在为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ENS)的入学考试做准备;在第一次考试失败后,他在第二次考试中通过,并于 1952 年被录取。在 ENS 的第一天,德里达遇到了路易斯·阿尔都塞,与他成为朋友。他的一位教授 扬·查内基Jan Czarnecki 是一名进步的新教徒,后来成为121 宣言的签署人。在参观了比利时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后(1953-1954 ) ,他完成了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硕士学位(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 [ fr ])。然后,他于 1956 年通过了竞争激烈的综合考试。德里达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助学金,他在 1956-57 学年在威德纳图书馆阅读了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 Ulysses)。1957年6月,他在波士顿与精神分析学家玛格丽特·奥库图里耶结婚。在1954 年至 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德里达要求在 1957 年至 1959 年间教授法语和英语,以代替服兵役。
战争结束后,从 1960 年到 1964 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教授哲学,在那里他是苏珊娜·巴切拉德Suzanne Bachelard (加斯顿的女儿)、乔治·坎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保罗·里库尔Paul Ricoeur(他在这些年创造了怀疑解释学一词)和让·瓦尔的助手。1963 年,他的妻子玛格丽特 (Marguerite) 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皮埃尔 ( Pierre )。1964 年,在路易斯·阿尔都塞 ( Louis Althusser )和让·伊波利特 (Jean Hyppolite ) 的推荐下,德里达在法国国立高等学校获得了永久性的教学职位,他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 1984 年。1965 年,德里达开始与泰尔奎尔Tel Quel文学和哲学理论家团体建立联系,持续了七年。德里达在 1971 年后与Tel Quel团体的疏远与他对他们拥护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持保留态度有关。
凭借“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他在 196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构主义座谈会上的贡献,使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国际知名度。在同一个座谈会上,德里达会见了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后者是未来几年的重要对话者。第二个儿子让 (Jean) 出生于 1967 年。同年,德里达出版了他的前三本书——《写作与差异》、《言语与现象》和《语法学》。
1980 年,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并被授予国家博士学位。他 1980 年的论文随后以英文译本出版,名为“The Time of a Thesis: Punctuations”。1983 年,德里达与肯·麦克马伦合作拍摄了电影《鬼舞》。德里达以他本人的身份出现在影片中,并为剧本做出了贡献。
德里达游历广泛,担任过一系列访问职位和永久职位。德里达从1984年起成为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正教授(1983年底当选)。1983 年,他 与弗朗索瓦·夏特莱 ( François Châtelet )等人共同创立了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CIPH;“国际哲学学院”),该机构旨在为学术界其他地方无法开展的哲学研究提供场所. 他被选为第一任主席。1985 年,西尔维亚娜·阿加辛斯基 (Sylviane Agacinski)生下了德里达的第三个孩子丹尼尔 (Daniel)。
1985 年 5 月 8 日,德里达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
1986 年,德里达成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人文学科教授,他一直在那里任教,直到 2004 年去世前不久。他的论文被归档在大学档案馆。德里达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儿子们表示,,他们希望UCI的档案副本与法国当代出版档案馆研究所共享。该大学曾提起诉讼,试图从德里达的遗孀和孩子们那里获得手稿和信件,它认为这位哲学家已经承诺收藏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它在2007年放弃了诉讼。
德里达是美国和欧洲其他几所主要大学的定期客座教授,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欧洲研究生院。
他被剑桥大学(1992 年)、哥伦比亚大学、新社会研究学院、埃塞克斯大学、天主教鲁汶大学、西里西亚大学、科英布拉大学、雅典大学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奖。
德里达在剑桥的荣誉学位遭到了分析传统中主要哲学家的抗议。包括蒯因、马库斯和阿姆斯特朗在内的哲学家写信给大学,“德里达的作品不符合清晰和严谨的公认标准”,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对理性、真理和学术价值的半可理解攻击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在一所杰出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的理由”。
在他生命的后期,德里达参与制作了两部传记纪录片,分别是Safaa Fathy的D’ailleurs, Derrida ( Derrida’s Elsewhere ) (1999), 和Kirby Dick和 Amy Ziering Kofman的Derrida (2002)。
德里达在 2003 年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这减少了他的演讲和旅行活动。2004 年 10 月 9 日凌晨,他在巴黎一家医院手术期间死亡。
在他去世时,德里达同意夏天去海德堡担任伽达默尔教授职位。当时的海德堡校长彼得·霍梅尔霍夫 (Peter Hommelhoff) 将德里达的地位总结为:“超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界限,他不仅是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而且是整个时代文化观念的领军人物。”
哲学
德里达称自己为历史学家。他质疑西方哲学传统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文化的假设。通过质疑主流话语并试图对其进行修改,他试图使大学场景民主化并将其政治化。德里达将他对西方文化假设的挑战称为“解构主义”。在某些场合,德里达将解构主义称为某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激进化。
通过详细阅读从柏拉图到卢梭再到海德格尔的作品,德里达经常认为,西方哲学不加批判地允许隐喻深度模型来支配其语言和意识的概念。他将这些通常未被承认的假设视为哲学所束缚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德里达认为,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创造了“标记的”或等级化的二元对立,它对从我们对语言与写作关系的概念到我们对种族差异的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有影响。解构主义试图揭露和破坏这种“形而上学”。
德里达将文本视为围绕二元对立构建的文本,如果它打算有任何意义,所有言论都必须表达出来。从广义上讲,这种文本方法受到索绪尔的符号学的影响。 被认为是结构主义之父之一的索绪尔认为,术语在语言内部与其他术语的相互决定中获得其意义。
也许德里达最常被引用和最著名的断言,出现在他的著作《语法学》 (Of Grammatology)(1967 年)中一篇关于卢梭的文章中: “没有脱离文本的东西”(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德里达的批评者经常被指责错误翻译了法语中的短语,暗示他写了“ Il n’y a rien en dehors du texte ”(“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并广泛传播了这个翻译,使人以为德里达是在暗示除了文字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德里达曾经解释说,这个断言“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解构主义的某种口号,总的来说理解得很糟糕……没有别的意思:语境之外没有东西。在这种形式下,它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这个公式无疑会不那么令人震惊。”
早期作品
德里达的职业生涯始于研究现象学的局限性。他的第一份冗长的学术手稿是作为他的高等研究文凭的论文,于1954年提交,涉及埃德蒙·胡塞尔的工作。加里·班纳姆 (Gary Banham) 曾说过,这篇论文“在许多方面是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最雄心勃勃的解释,不仅在所涉及的作品数量方面,而且在其调查的异常集中的性质方面”。1962年他出版了埃德蒙·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言》,其中包含他自己翻译的胡塞尔论文。德里达思想的许多元素已经出现在这部作品中。
德里达于 1966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首次在法国以外受到广泛关注(随后被收录在《写作与差异》一书中)。发表这篇论文的会议关注的是结构主义,当时它在法国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在美国才刚刚开始受到关注。德里达与其他参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结构主义缺乏明确的承诺,他已经对运动持批评态度。他赞扬了结构主义的成就,但也对其内部局限性持保留态度;这导致美国学者将他的思想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
德里达论文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到 1970 年会议论文集出版时,该文集的标题变成了《结构主义之争》。在这次会议上,他还遇到了保罗·德曼,他将成为他的密友和巨大争议的来源,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德里达与拉康的作品有着复杂的关系。
现象学与结构主义辩论 (1959)
1960 年代初,德里达开始公开演讲和写作,解决当时最热门的辩论。其中之一是新的和日益流行的结构主义运动,它被广泛认为是现象学方法的继承者,后者是由胡塞尔在 60 年前发起的。在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德里达对这个问题的逆流看法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将讨论从庆祝结构主义的胜利重新调整为“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的辩论”。
胡塞尔所设想的现象学是一种哲学探究的方法,它摒弃了自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偏见,支持一种揭示个人“生活经验”的反思性关注方法;对于那些有更多现象学倾向的人来说,其目标是通过理解和描述经验的起源,即从一个起源或事件中出现的过程来理解经验。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经验的“深度”实际上只能是结构本身不是经验性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德里达在 1959 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每个结构或“共时性”(synchronic)现象都有一段历史,如果不了解其起源就无法理解结构。同时,为了产生运动或潜力,起源不能是某种纯粹的统一或简单,而必须已经明确表达——复杂——这样才能从中出现一个“历时性”(diachronic)过程。这种原始的复杂性不能被理解为原始的定位,但更像是起源的默认值,德里达将其称为可迭代性、铭文或文本性。(iterability, inscription, or textuality.)正是这种原始复杂性的思想推动了德里达的工作,并从中衍生出所有术语,包括“解构”。
德里达的方法包括展示这种起源复杂性的形式和种类,以及它们在许多领域的多重后果。他通过对哲学和文学文本进行彻底、仔细、敏感但又具有变革性的阅读来实现这一点,以确定这些文本的哪些方面与它们表面的系统性(结构的统一性)或预期的意义(作者的起源)相悖。通过展示思想的困境和间隙(aporias and ellipses),德里达希望展示这种起源的复杂性的无限微妙的方式,根据定义,这种复杂性永远不可能被完全了解,它产生了结构化和破坏性的效果。
1967–1972
德里达的兴趣跨越了学科界限,他对各种不同材料的了解反映在 1967 年出版的三部作品集中:《言语与现象》、《文字学》(最初作为Maurice de Gandillac 的博士论文提交),和《写作与差异》。
德里达多次承认他受惠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表示没有他们,他不会说一个字。在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意义’,它与据称在‘声音’标题下确定为存在价值、对象存在、意义对意识的存在、在所谓的活生生的言语和自我意识中的自我存在有什么历史关系?”(what are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to what is purportedly identified under the rubric ‘voice’ as a value of presence, presence of the object, presence of meaning to consciousness, self-presence in so called living speech and in self-consciousness?”)在另一篇题为“暴力与形而上学:关于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思想的论文”的文章中,德里达思想的另一个主要主题的根源出现了:“解构分析剥夺了当下的威望,并将其暴露于某种标榜自己之外的东西:“完全的他者”,超越了从当下可以预见的东西,超越了“同一”的视界。”(”Deconstructive analysis deprives the present of its prestige and exposes it to something tout autre, “wholly other,” beyond what is foreseeable from the present, beyond the horizon of the “same”)除了卢梭、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外,这三本书讨论和/或依赖了许多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语言学家索绪尔、黑格尔、福柯、巴塔耶、笛卡尔、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古生物学家勒罗伊·古尔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以及作家贾布里斯和阿尔托。
这部 1967 年出版的三本书阐述了德里达的理论框架。德里达试图接近西方知识传统的核心,将这一传统描述为“寻找作为意义起源或保证的先验存在”。海德格尔将“将构成世界的意义关系置于所有关系之外的实例”的尝试称为逻辑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哲学事业本质上是逻辑中心主义,这是从犹太教和希腊主义继承而来的范式。他反过来将逻各斯中心主义描述为父权制和男性主义。德里达对“理解西方文化中某些深藏不露的哲学预设和偏见”做出了贡献,认为整个哲学传统都建立在任意的二分法类别上(如神圣/亵渎、能指/能指、思想/身体),并且任何文本都包含隐含的层次结构,“通过这种层次结构,一种秩序被强加于现实,并通过这种层次结构进行微妙的压制,因为这些层次结构排除、从属和隐藏各种潜在的意义。” 德里达将他揭示和解开这些二分法的程序称为对西方文化的解构。
1968年,他在法国杂志Tel Quel上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论文《柏拉图的药房》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德里达于 1972 年出版的三本书之一的《传播》中,(另外两本:散文集《哲学边缘》和题为《立场》的访谈集。)
1973–1980
从 1972 年开始,德里达平均每年出版一本书以上。德里达继续创作重要作品,,如《格拉斯》(1974)和《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超越》(1980)。
1972年后,德里达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是美国几所主要大学的定期客座教授和讲师。80年代,在美国文化战争期间,保守派就德里达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遗产展开了争论,并声称他对美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影响超过学术哲学家。
精神(1987)
1987 年 3 月 14 日,德里达在 CIPH 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海德格尔:未决问题”的演讲,该演讲于 1987 年 10 月作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出版。它遵循海德格尔作品中Geist (精神)的角色转变,并指出,在 1927 年,“精神”是海德格尔着眼于拆解的哲学术语之一。然而,随着他在 1933 年参与纳粹政治,海德格尔成为“德国精神”的拥护者,直到 1953 年才退出对该术语的崇高解释。德里达问道,“这期间呢?” 德里达的书在许多方面与他长期接触海德格尔有关(例如哲学边际中的“人的终结”,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于哲学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巴黎研讨会,以及以Geschlecht和Geschlecht II的英文形式发表的论文。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的 “四条指导线 “构成 “这个Geflecht[编织]的结:”问题的问题”,”技术的本质”,”动物性的话语”,以及 “时代性 “或 “隐藏的目的论或叙述秩序”。
Of Spirit促成了关于海德格尔纳粹主义的长期争论,并与一位以前不为人知的智利作家维克多·法里亚斯在法国出版的一本书同时出版,他指责海德格尔的哲学等于全心全意地支持纳粹 冲锋队(SA)派。德里达在一次采访《海德格尔,哲学家的地狱》和随后的一篇文章《对理由的评论?如何用理由来掩饰?》中回应了法里亚斯,他称法里亚斯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薄弱读者,并补充说法里亚斯和他的支持者吹捧为新证据的许多证据在哲学界早已为人所知。
1990 年代:政治和伦理主题
一些人认为德里达的作品在 1990 年代发生了政治和伦理上的“转变”。被引用作为这种转变证据的文本包括《法律的力量》 (1990)、《马克思的幽灵》 (1994) 和《友谊的政治》(1994)。有些人将《死亡的礼物》视为他开始更直接地将解构应用于伦理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证据。在这项工作中,德里达解释了圣经中的段落,特别是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牺牲,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抖》。
然而,伦纳德·劳勒(Leonard Lawlor)、罗伯特·马格里奥拉(Robert Magliola)和妮可·安德森(Nicole Anderson)等学者认为,这种“转向”被夸大了。]包括德里达本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在他的“政治转向”期间所做的大部分哲学工作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论文。
德里达发展了一种关于好客的伦理学观点,探索了存在两种类型的好客的想法,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尽管这为许多学者的著作做出了贡献,但德里达却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德里达对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沃尔特·本雅明、卡尔·施密特、扬·帕托卡的当代解读,主题包括法律、正义、责任和友谊,对哲学以外的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影响了美学、文学批评、建筑学、电影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法律、精神分析、神学、女权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和政治理论。让-吕克·南希、理查德·罗蒂、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罗莎琳德·克劳斯、海伦娜·西克斯、朱莉娅·克里斯特娃、邓肯·肯尼迪、加里·佩勒、德鲁西拉·康奈尔、艾伦·亨特、海登·怀特、马里奥·科皮奇和阿伦·芒斯洛是一些受到解构影响的作家。
德里达在列维纳斯的葬礼上发表了悼词,后来出版了《再见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这是对列维纳斯道德哲学的欣赏和探索。德里达借鉴了布拉查·L·埃廷格对列维纳斯女性气质概念的解释,并改变了他自己早先对该主题的解读。
德里达继续创作文学读物,撰写了大量关于莫里斯·布朗肖、保罗·策兰等人的文章。
1991 年,他出版了《另一个标题》,其中他讨论了身份的概念(如文化身份、欧洲身份和民族身份),以其名义在欧洲发动了“最严重的暴力”、“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宗教或民族主义狂热的罪行。”
在 1997 年的塞里西会议Cerisy 会议上,德里达就“自传体动物”的主题发表了十个小时的演讲,题为“因此我是动物”。围绕非人类动物的本体论、动物屠宰的伦理学以及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等问题,这篇演讲被视为开启了德里达哲学晚期的“动物转向”,尽管德里达本人曾表示他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动物出现在他最早的作品中。
哀悼之作(1981–2001)
从1981年的《罗兰·巴特之死》开始,德里达制作了一系列关于因失去朋友和同事而引起的哀悼和记忆的文本。《保罗·德曼回忆录》是一本书长的系列讲座,首先在耶鲁大学,然后在欧文大学,作为德里达的韦莱克讲座,随后于1986年出版,1989年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像贝壳深处的海洋之声:保罗·德曼的战争》。最终,14篇论文被收录在《哀悼之作》(2001年)中,并在2003年的法语版《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字面意思是“每次都独一无二,世界末日”)中进行了扩展,其中包括献给Gérard Granel和Maurice Blanchot的文章。
2002年电影
2002 年 10 月,在电影《德里达》的院线首映礼上,他说,在很多方面,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盖伊·德波的作品,这种接近体现在德里达的文本中。德里达特别提到,“我所说的关于媒体、技术、奇观和‘表演批评’的一切,可以这么说,还有市场——一切都成为奇观,以及对奇观的利用。” 在德里达提到奇观的地方,有一处是 1997 年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访谈。
与让·鲍德里亚辩论
2003 年 2 月 19 日,随着2003 年对伊拉克的入侵迫在眉睫,勒内·梅杰[法]主持了让·鲍德里亚和德里达之间的一场题为“为什么今天会有战争(Pourquoi La Guerre Aujourd’hui?)”的辩论,由梅杰精神分析高级研究所和《世界外交报》共同主办。辩论讨论了恐怖袭击与入侵之间的关系。[127] [128]
政治
德里达参与了许多政治问题、运动和辩论:
- 尽管德里达参加了1968年5月抗议活动的集会,并在高等师范学院组织了第一次大会,但他说:“面对某种自发性的崇拜、融合主义者、反工会主义者的狂热,面对最终“自由”的言论、恢复“透明度”的热情,我仍在保持警惕,甚至感到担忧。”,他经常与莫里斯·布兰肖会面。
- 他在美国发表《人类的终结》时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意见。
- 1977 年,他与福柯和阿尔都塞一起签署了反对同意年龄法的请愿书。
- 1981 年,在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等人的推动下,德里达 (Derrida ) 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共同创立了法国扬·胡斯协会其目的是帮助持不同政见或受迫害的捷克知识分子。德里达成为副主席。
- 1981 年底,他在未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布拉格主持了一次会议,随后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并被指控“生产和贩卖毒品”,他声称这些毒品是他在访问卡夫卡的坟墓时种植的。在密特朗政府的干预和米歇尔·福柯的协助下,他被释放(或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称之为“驱逐”),于1年1982月133日返回巴黎。
- 他在 1984 年表达了对核武器扩散的担忧。
- 从 1983 年开始,他代表纳尔逊·曼德拉积极参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文化活动。
- 他在 1988 年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会见了巴勒斯坦知识分子。
- 他抗议死刑,在晚年致力于为废除死刑提出非功利主义的论据,并积极参与释放穆米亚·阿布·贾马尔的运动。
- 1995年,德里达加入了一个支持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社会党候选人资格的委员会,执勤未曾参加过任何传统的选举政党,他表示对这种组织的疑虑可以追溯到他在ENS读书时的共产主义组织努力。
- 在2002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他拒绝在极右翼候选人让-玛丽·勒庞和中右翼的雅克·希拉克之间的决选中投票,理由是缺乏可接受的选择。
- 虽然在9/11 恐怖袭击后支持美国政府,但他反对2003 年入侵伊拉克。
除了这些明确的政治介入之外,德里达还致力于在哲学内外重新思考政治和政治本身。德里达坚持认为,从他职业生涯的一开始,一种明显的政治色彩就弥漫在他的文本中。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试图理解责任、国家理性、他者、决定、主权、欧洲、友谊、差异、信仰等概念的政治含义的尝试变得更加明显。到 2000 年“民主即将到来”的理论化和对现有民主国家的局限性的思考已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对德里达的影响
他青春期的重要读物是卢梭的《孤独行者的遐想》和《忏悔录》 、安德烈·纪德的日记、 《东大地的滋养》、《陆地上的营养》和《不道德的人》,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特别是启发德里达青少年时期的一句话,是吉德的《大地的滋养》第四卷中的著名诗句:家人,我恨你!在 1991 年的一次采访中,德里达评论了同样来自纪德同一部作品第四卷的类似诗句:“我讨厌家园,家庭,所有人们认为他会找到休息的地方”(Je haïssais les foyers, les familles , tous lieux où l’homme pense trouver un repos )。
其他对德里达产生影响的还有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索伦·克尔凯郭尔、亚历山大·科耶夫、莫里斯·布朗肖、安东尼·阿尔托、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埃德蒙·胡塞尔、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费迪南·德·索绪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JL·奥斯汀和斯特凡·马拉美。
他在《告别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一书中揭示了他受到这位哲学家和塔木德学者的指导,他以 “脸 “的形式实践了与他者的现象学相遇,并命令人类做出反应。使用解构法来阅读犹太文本–如《塔木德》–是比较罕见的,但最近已经有人尝试了。
同行和同时代人
德里达的哲学朋友、盟友、学生和德里达思想的继承人包括保罗·德曼、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路易斯·阿尔都塞、伊曼纽尔·莱维纳斯、莫里斯·布兰肖、吉尔·德勒兹、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莎拉·科夫曼、海伦娜·西克斯、伯纳德·斯蒂格勒、亚历山大·加西亚·杜特曼、约瑟夫科恩、杰弗里·本宁顿、让-吕克·马里昂、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拉斐尔·扎古里-奥利、雅克·埃尔曼、阿维塔尔·罗内尔、朱迪思·巴特勒、贝阿特里斯·加利农-梅伦内克、埃内斯托·拉克劳、塞缪尔·韦伯、凯瑟琳·马拉布和克劳黛特·萨蒂利奥特。
南希和拉库-拉巴特
让-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是德里达在法国的第一批学生,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著名的重要哲学家。尽管他们在主题上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通常在方法上也存在差异,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德里达的密切互动仍在继续。
德里达写了关于他们两人的文章,包括一本关于南希的长书:让-吕克·南希(On Touching-Jean-Luc Nancy,2005)。
保罗·德曼
德里达在思想生活中最著名的友谊是与保罗·德曼的友谊,这种友谊始于他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会面,一直持续到德曼于 1983 年去世。德曼提供了一种稍微不同的解构方法,他对文学和哲学文本的阅读是对培养一代读者至关重要。
德曼死后不久,德里达写了《回忆录:为保罗·德曼而战》一书,并于1988年在《批判性探究》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像贝壳深处的大海的声音:保罗·德曼的战争”。这本回忆录引起了争议,因为在德里达发表他的作品之前不久,比利时文学评论家奥尔特温·德·格雷夫发现,早在他在美国从事学术生涯之前,德曼就已經在德國佔領比利時期在一家親納粹報紙上寫了近兩百篇文章,其中幾篇是明確的反猶主義。
德里达的批评者认为,德里达淡化了德曼作品中的反犹太主义特征。一些批评家发现德里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令人惊讶,因为例如,德里达也公开反对反犹太主义,并且在 1960 年代因博夫雷的反犹太主义事例而与海德格尔的弟子让-博夫雷决裂。
米歇尔·福柯
德里达对福柯的批评出现在论文《我思与疯狂的历史》(来自《写作与差异》)中。1963 年 3 月 4 日,在福柯参加的瓦尔哲学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它首次以演讲的形式发表,并在两人之间造成了从未完全修复的裂痕。
在 1972 年版的《疯狂史》的附录中,福柯质疑德里达对其作品的解释,并指责德里达实践“一种历史确定的小教学法 […]它告诉学生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 一种教学法,它反过来赋予大师们无限的主权,使其可以无限期地重述文本。”根据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 (Carlo Ginzburg)的说法,福柯可能部分地在德里达批评的刺激下写下了《事物的秩序》 (1966) 和《知识考古学》。 Carlo Ginzburg 认为德里达在《我思与疯狂史》中的批评简单地标记为“轻率的、虚无主义的反对”,而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论证
马歇尔·麦克卢汉
德里达熟悉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的作品,自从他 1967 年初的著作(语法学,言语和现象)以来,他将语言称为“媒介”,将语音文字称为“伟大形而上学的媒介,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冒险。”
对于麦克卢汉关于写作终结的意识形态,他表达了他与麦克卢汉的不同意见。在 1982 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
我认为麦克卢汉话语中有一种我不同意的意识形态,因为他对恢复口语社区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这将摆脱写作机器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神话,可以追溯到……比方说柏拉图、卢梭……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写作的尽头,我认为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生活在写作的延伸——压倒性的延伸——中。至少在新意义上…我指的不是按字母顺序书写,而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那些书写机器(例如录音机)的新含义。这也是写作。
在他 1972 年的论文《签名事件背景》Signature Event Context中,他说:
写作,交流,如果人们坚持保留这个词的话,沟通就不是意义的传递、意图和意义的交流、话语和“意识的交流”。我们没有看到写作的结束,而按照麦克·卢汉的意识形态表述,这将恢复社会关系的透明度或直接性;但事实上,一种越来越有力的历史性书写,其言语、意识、意义、存在、真理等系统只能是一种效果,并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正是这种被质疑的效果,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逻辑中心主义。
建筑思想家
德里达对二十世纪末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和伯纳德·屈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德里达影响了一个由艾森曼在Chora L Works提出的一个项目:雅克·德里达和彼得·艾森曼。这个设计是由Tschumi为巴黎的Parc de la Villette构思的,其中包括一个筛子或竖琴状结构,德里达设想将其作为khôra容器状特性的物理隐喻。此外,德里达对柏拉图在蒂玛乌斯(48e4)中设定的khôra(χώρα)概念的评论后来在现象学领域的哲学作品和建筑著作中得到了反思。
德里达用“χώρα”来命名一种为存在“让位”的激进的他者。El-Bizri 在此基础上更狭义地使用khôra来命名存在与存在之间本体论差异的激进事件。埃尔-比兹里对“khôra”的反思被作为处理海德格尔思想中对居住、存在和空间的沉思的基础,以及空间和地点的批判概念,因为它们在建筑理论(及其在现象学思维中的分支)和哲学和科学史中的发展,重点是几何学和光学。这也描述了比兹里对“生态学”的看法,作为海德格尔通过地球-天空-凡人-神性(Erde und Himmel,Sterblichen und Göttlichen)的四重(Das Geviert)对存在(Seinsfrage)问题的考虑的延伸;也受到他自己对德里达对“χώρα”的看法的沉思的影响。因此,生态学与本体论相互纠缠在一起,世俗的存在分析以泥土为基础,而环境主义则以本体论思维为导向。德里达认为主体就像柏拉图的khôra,希腊语的空间、容器或场所。柏拉图提出khôra介于可感性和可理解性之间,一切都经过它,但没有任何东西保留在其中。例如,一个图像需要被某种东西支撑,就像一面镜子需要反射一样。对于德里达来说,khôra无视命名或他“解构”的非此即彼逻辑的尝试。
批评
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在一篇题为《代笔》的论文中,将德里达的《语法学》(De la grammatologie)翻译成英文的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批评了德里达对马克思的理解。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评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时写道:“预兆在本书的文字中根深蒂固,就像一个戏剧性的反问句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语法紧随另一个问题之后,使自己对模仿敞开了大门。
英语哲学家的批评
尽管德里达在 1988 年至少在美国哲学协会发表过一次演讲, 并受到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亚历山大·尼哈马斯 ( Alexander Nehamas ) 和斯坦利·卡维尔 ( Stanley Cavell)等当代哲学家的高度评价,但他的工作被其他分析哲學家,如約翰·塞爾(John Searle)和威拉德·凡·奧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視為偽哲學, 或诡辩。
事实上,至少从1980年代开始,一些分析哲学家就声称德里达的作品“不是哲学”。他们给出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声称德里达的影响不是针对美国哲学系,而是针对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
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在其 1989 年出版的《偶然性、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中指出,德里达(尤其是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以后》中,其中一部分是小说实验)有目的地使用无法定义的词语(例如,差异différance),并在足够多样化的上下文中使用以前可定义的单词,以至于无法理解,这样读者就永远无法理解德里达的文学自我。然而,罗蒂认为这种有意的混淆是有哲学根据的。在混淆他的信息时,德里达试图逃避他的前辈天真的、积极的形而上学计划。
罗杰·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在 2004 年写道,“他很难总结,因为这是无稽之谈。他认为,符号的意义从未在符号中揭示,而是无限期地推迟,并且符号仅凭借其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才有意义。对于德里达,没有意义这样的东西——它总是躲避我们,因此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关于德里达的学识和写作风格,诺姆乔姆斯基写道:“我发现这种学识令人震惊,因为它是基于可悲的误读;而论点,就其本身而言,未能接近我几乎从孩提时代就熟悉的那种标准。好吧,也许我错过了什么:可能是,但如前所述,怀疑仍然存在。”
保罗·R·格罗斯(Paul R.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也在《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吵》(1994)中批评他滥用科学术语和概念。
三场争吵(或争端)尤其走出了学术圈,并得到了国际大众媒体的报道:1972-88 年与约翰·塞尔的争吵;分析哲学家对剑桥大学施加压力,要求不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以及与理查德的争执沃林和 NYRB。
剑桥名誉博士学位
1992 年,剑桥大学的一些学者(大多数不是来自哲学系)提议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这遭到了该大学哲学教授休·梅勒(Hugh Mellor)等人的反对。来自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和英国机构的其他十八位哲学家,包括巴里·史密斯、威拉德·范·奥曼·奎因、大卫·阿姆斯特朗、露丝·巴坎·马库斯和勒内·汤姆,随后致函剑桥,声称德里达的作品“不符合公认的清晰和严谨标准”,并将德里达的哲学描述为由“类似于达达主义者的技巧和噱头”组成。这封信的结论是:
..即使有连贯的断言,这些断言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认为,基于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对理性、真理和学术价值的半可理解的攻击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在一所杰出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的充分理由。
最终,当剑桥大学将动议付诸正式投票时,支持者的人数超过了抗议者——336 票对 204 票;尽管几乎所有提议德里达并投赞成票的人都不是来自哲学系。休·梅勒继续认为这个奖项不配,他解释说:“他是一个平庸的、没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甚至不是有趣的坏人”。
德里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作品受到攻击的部分原因是它质疑和修改了“主流话语的规则,它试图将教育和大学场景政治化和民主化”。为了回答有关“特殊暴力”、强迫性“凶猛”和“攻击”的“夸大”的问题,他会说这些批评家在他的案例中组织和实践了“一种强迫性的个人崇拜,哲学家应该知道如何质疑,最重要的是要温和”。
与理查德·沃林和纽约时报的争端
理查德沃林自 1991 年以来一直认为,德里达的作品以及德里达的主要灵感来源(例如,巴塔耶、布朗肖、列维纳斯、海德格尔、尼采)导致了腐蚀性的虚无主义。例如,沃林认为“推翻和重新命名的解构姿态最终威胁要抹去纳粹主义与非纳粹主义之间的许多本质区别”。
1991年,当沃林在《海德格尔之争》第一版中发表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访谈时,德里达辩称该访谈是故意恶意的误译,“明显可恶”和“软弱、简单化和强迫性侵略”。由于法国法律要求翻译必须征得作者的同意,而这种同意并未给予,德里达坚持该访谈不得出现在任何后续版本或再版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随后拒绝提供重印或新版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之争》的后期版本也省略了对德里达的采访。由于海德格尔学者托马斯希恩对沃林的书的友好评论,此事得以公开曝光出现在《纽约书评》中,希恩在其中将德里达的抗议描述为审查制度的强制实施。随后进行了书信往来。德里达在《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工作(坏例子:纽约书评和公司如何做生意)》中反过来回应了希恩和沃林,该书发表在《要点》一书中。
二十四位来自不同学派和团体的学者——他们往往彼此意见不一,也反对解构——签署了一封致《纽约书评》的信,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该杂志以及希南和沃林的行为的愤慨。
重要讣告
德里达的重要讣告发表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独立报上。国家》杂志对《纽约时报》的讣告作出回应称,“尽管美国报纸此前曾蔑视和贬低德里达,但对于一位深刻影响了两代美国人文学科的国际知名哲学家的讣告,语气似乎特别刻薄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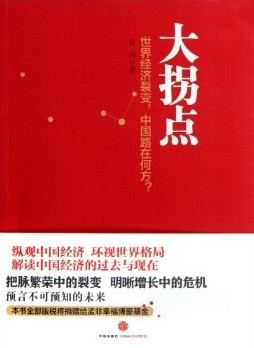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