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 2016年08月31日 14:38浏览 18.7w来源:界面新闻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诗人”的茨维塔耶娃(1892年10月8日-1941年8月31日)。
编者按:我们所知晓的茨维塔耶娃,无疑具备着那一时代俄罗斯作家所共有的某种困厄与悲剧性,除此之外,她的爱情与家庭之艰辛赋予了她更为独特和深切的悲剧色彩:丈夫应征入伍,一别五年渺无音讯,小女儿饿死在育婴院中,后与丈夫团聚,流亡欧洲,20世纪三十年代末返回祖国后,大女儿阿莉娅被捕,随即被流放,丈夫遭到枪决,她一边从事诗歌翻译,一边以帮厨和清扫换取口粮、维持生活,1941年8月31日,在极端的孤立和痛苦中,茨维塔耶娃自缢身死。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写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似是一语成谶,也仿佛她生命的注脚。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乱世之中,大女儿阿莉娅与她相伴,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她的诗歌基因,茨维塔耶娃曾为年幼的阿莉娅写下诗歌:“在严酷的未来,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在同一张破木桌上缝补与写诗,她会在写作过程扭过头去问身边的阿莉娅:“你说,剧本最后的一个词,该是什么呢?”“最后一个词,当然应该是——爱!”这位第一读者当时只有七岁。她们共享精神生活,阿莉亚不称呼茨维塔耶娃“妈妈”,而是直呼“玛丽娜”。阿莉娅早慧而冷静,小小年纪便开始与阿赫玛托娃阿姨、帕斯捷尔纳克叔叔等人通信联络,如同老友一般。
在阿莉娅的《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她以相叠的短句回忆与刻画妈妈,简洁有力,如同一把版画刻刀,寥寥几笔,笔笔不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三,体形跟埃及男孩子相像,肩膀宽阔,胯骨窄小,腰身纤细。少女时的圆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变得结实、消瘦,有贵族气质;她的踝骨和脚腕部位又硬又细,走起路来,步子轻快,举手投足动作频率极快,但是并不猛烈。当着人的面,感觉有人在看她,甚至频频注视她的时候,她会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尽力显得更温和。那时候,她的手势会变得小心谨慎,有所节制,但是从来不会拘谨呆板。
她的姿态一向端庄严肃,即便坐在书桌边低头看书,她的脊椎也不弯曲,“脊椎骨如钢铁铸就的一般”。
她的头发,颜色界于金色和深棕色之间,年轻时,头发柔软,卷曲如波浪,很早就出现了白发,这一点再次说明,她常在户外活动,由于光线照射,她的脸色微微发黑,因缺乏光泽又显得有些苍白;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像葡萄一样,目光明亮,褐色的眼皮很少眨动。
![图片[1]-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 终生孤独无助-人文百科](https://img2.jiemian.com/101/original/20160831/147262529397205500_a700xH.jpg)
面部的五官轮廓线条准确、清晰;如果比喻为雕塑,那么雕塑师考虑周到,没有任何疏忽,没有一刀飘忽游移,没有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 鼻子,鼻梁不宽,微微有点儿隆起,鼻端不尖不翘,鼻翼平缓,下面两个活动的鼻孔像翅膀一样自然,嘴巴显得柔软,双唇之间形成一条无形的曲线。
眉宇间有两条纵向的皱纹,两边是淡褐色的眉毛。
面孔初看上去孤僻、冷静,其实充满了内在的变化,隐含着丰富的表情,像天空,像水,瞬息万变。可惜,很少有人能读懂这张面孔的表情。
双手结实、干练、惯于劳动。两枚银戒指(一枚刻有小轮船图案,平滑的圆环上镶着玛瑙宝石雕刻的赫尔墨斯像,那是她父亲送的礼物),还有订婚戒指——三枚戒指一直戴在手指上,从不摘下来,三枚戒指并不引人注目,并非为了装饰,也不想束缚双手,而是很自然地跟双手融合为一个整体。
声音像女孩子一样高亢、响亮、柔韧。
语言——凝练,对话——准确。
善于倾听;交谈时从不盛气凌人,压制对方,但争论起来很可怕: 在辩论、争论、讨论当中,态度恭敬而冷峻,常以闪电般的攻击置论敌于死地。
讲起故事来极其精彩。
她朗诵诗歌不像室内音乐,而像面对大庭广众。
朗诵富有激情,若有所思,不“故意压低声音”,诗行末尾从来不降低音调;即便最复杂的内容一瞬之间能表达得脉络清晰。
喜欢主动、热情地朗诵,只要有人请求,甚至不等请求,自己出面说:“想不想听我来给你们朗读诗歌?”
终生迫切需要读者,需要听众,对此永不满足,写完的作品,需要迅速、直接的反响。
![图片[2]-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 终生孤独无助-人文百科](https://img2.jiemian.com/101/original/20160831/147262539180001100_a700xH.jpg)
对待刚刚起步的诗人,态度和蔼,无比宽容,只要从他们身上发觉(或者想象)“天才的火花”;每每把这样的人看作兄弟,看作继承人——不是自己的继承人!而是诗歌的继承人!但是,一旦认清对方的渺小,便会毫不留情地断绝来往,无论他们处于开始阶段,还是已经达到了虚荣的巅峰。
她的为人确实善良、慷慨: 乐于帮助、支援、救济别人,恨不得使出浑身力量;最后的急需物品,能跟别人分享,因为她没有多余的东西。
善于付出,善于索取,不讲客套;长时间相信“善有善报”,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绵延不尽的伟大人性。
从来不软弱无力,但终生孤独无助。
对外人,态度谦卑,对亲人、朋友、孩子,像对自己一样,要求严格,甚至过分严厉。
她对时尚并不反感,不像有些见解肤浅的同时代人所非议的那样,不过,她没有物质条件享受时尚,追求时尚;她爱整洁,厌恶模仿时尚的伪劣赝品,侨居国外期间,为了尊严,她甚至常穿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服装。
对于物品,最看重的是它的结实耐用: 不喜欢容易破碎、容易损坏的东西,一句话,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物品”。
上床就寝很晚,睡觉前看书,很早起床。
习惯于斯巴达式的简朴,饮食不太讲究。
抽烟: 在俄罗斯——抽自己卷的烟卷儿,到了国外——抽男人们抽的气味呛人的香烟,一次抽半支烟卷儿,使用樱桃木雕刻的普通烟嘴。
喝不加奶的咖啡: 把浅色的咖啡豆炒成深褐色,很耐心地磨咖啡,使用老式的土耳其小磨子,铜制的,状如圆柱,上面刻有东方的花纹图案。
天生与大自然血肉相连,她爱大自然——爱山峦、爱悬崖、爱森林——如同多神教教徒,奉大自然为神灵,自然征服了她,发自内心的挚爱,不掺杂任何直觉,因此,面对大海,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既不能步行穿越,又不会下水游泳。木然的观赏,她又不喜欢。
平原上呆板的风景让她沉闷厌倦,就像看到沼泽里灰蒙蒙的芦苇地那种感觉,又像一年当中潮湿的月份,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仿佛随时可能陷进去似的,远处的地平线摇摇晃晃。
在她的记忆当中,永远感到亲切的是童年的塔鲁萨,年轻时的科克捷别里,她一直在寻找,偶尔会发现类似的风景,比如莫顿森林丘陵起伏的“皇家狩猎园区”,还有地中海沿岸一带山岭连绵的景色和气息。
她不太害怕炎热,却特别害怕寒冷。
对于剪下来的花枝、花束,对于开放在花瓶里或养在窗台上陶瓷盆里的花,她一向态度冷淡;她更喜欢生长在花园里的花朵,喜欢常春藤、野生杜鹃、野葡萄藤、灌木丛,看重它们枝干遒劲,寿命长久。
她珍视人对自然的明智干预,赞赏人与自然合作的产物——公园、堤坝、道路。
对待狗和猫,她始终如一地满怀温情、亲切、理解(乃至尊重!),狗和猫也以同样的情感回报她。
外出散步,常常预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走到某个地点,攀登到某个高度;得到“猎获物”比看到买来的东西更高兴: 摘采的蘑菇、浆果,在捷克期间,生活艰难,当时我们住在城市郊区贫困的乡村,能拣到干树枝就很开心,点火炉有用。
在城市里常常转向,有时在熟悉的街道也会走错路,这让她常生闷气,可一旦到了城外,她的方向感却很好。
她害怕高楼,害怕人群(拥挤),害怕汽车、电梯、自动扶梯。在所有的城市交通工具当中,只敢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独自出门,无人陪伴)。如找不到公共汽车和地铁,宁愿步行走路。
缺乏数学才能,对任何技术都没有兴趣。
痛恨日常家务——恨它没完没了,难以脱身,恨它无谓重复,天天操心,恨它大量占用时间,妨碍必须做的正经事。但是,耐着性子,克制反感,还得操持家务——操持了一辈子。
喜欢交往,殷勤好客,爱主动结识朋友,不喜欢跟熟人断绝联系。疏远由“一贯正确的人”组成的团体,更爱接近脾气古怪者形成的圈子。何况她本人就以“怪人”闻名。
无论友好,还是敌对,往往爱走极端,爱恨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不为自己树立偶像”,时常违反这一戒律。
体谅青少年,尊重老年人。
讲究幽默感,但明显可笑,或者粗俗的玩笑,在她看来并不可笑。
对她的童年产生影响的两种因素——造型艺术(父亲的领域)和音乐艺术(母亲的领域),——她接受了音乐。形式与色彩,——凭借触觉和视觉获得的印象,她无动于衷。能够吸引她的只有故事情节,就像“小孩子看图画”一样,因此,跟油画相比,书里的插图,尤其是版画,更接近她的欣赏趣味。
早期一度迷恋戏剧,部分原因是受她年轻丈夫以及年轻朋友们的影响,不过这种痴迷仅限于在俄罗斯的青春时期,等到国外以后,随着年龄的成熟,她就不再关注戏剧了。
在所有供人观赏的艺术形式当中,她最喜欢电影,有趣的是,爱无声电影胜过有声电影,在她看来,无声电影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有利于创作,有利于感觉。
对于从事创作的人,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同行的敬意;游手好闲、寄生性的吃喝玩乐,最让她反感,让她同样厌烦的还有散漫、懒惰、空话连篇。
她是擅长驾驭语言的人,擅长行动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始终为人谦逊,了解自己的价值。
![图片[3]-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 终生孤独无助-人文百科](https://img1.jiemian.com/101/original/20160831/147262541966644300_a700xH.jpg)
她怎样写作?
天还不亮,一大早就起床,头脑清晰,干瘪的肚子空空,把所有不可推脱的事情,逐一开列出清单。给自己杯子里注满滚开的、不加奶的咖啡,把它放在书桌上,一生当中,每天都要坐在书桌前,像工人守着机床——怀着责任感,习以为常,万难更改。
面对书桌的时刻,其他的一切事务均属多余,统统放到一边,心无旁骛,机械性的动作,这地方只容得下手稿本和胳膊肘。
手掌托着前额,手指伸进头发里,转瞬间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闭目塞听,除了手稿,对一切都不闻不问,思绪和笔尖,全都渗入了稿本。
她不用零散的稿纸写作——要写,就写在稿本上,随便什么样的本子——从学生的练习册到记账用的账本,只要墨水不洇就行。在动荡的革命年代,草稿本都是她亲手制作、用线缝起来的。
她写作使用普通的木干蘸水笔,笔尖细小(学生使用的)。她从来不用自来水钢笔。
时不时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一支,偶尔喝口咖啡。推敲词语是否合适,常喃喃自语,或读出声音来。为寻找稍纵即逝的词句,不会突然跳起来,也不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书桌前面,一动不动,像钉在那里一样。
写重要作品,如灵感来临,思路顺畅,则书写起来异常迅速;若是写诗打草稿,寻找最确切的字眼儿、形容词、韵脚,或者修改、审核已经写出来的初稿,删削冗长啰嗦或含混不清的词句,那就一动不动,凝神思考。
为追求表达精确,语意和音响谐调一致,一页接一页写满了押韵的诗行,有的诗行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要删去的诗行,通常并不一笔勾掉,而是在下面画条线,然后寻找新的诗句。
在着手创作一部重要作品之前,尽最大努力把构思具体化,写出提纲,有所遵循,不随意偏离,不让题材自身的发展衍变超出主观意愿,变得难以把握掌控。
她写字的笔体非常独特,字母写得圆圆的、小小的,字迹倒很清晰,三十二三岁以后,她的手稿使用缩写词越来越多,很多词只用头一个字母表示,读起来很难辨认;因此,很多草稿成了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看懂的手稿。
有个性的笔体,早在童年时便已经确立下来。
通常说来,她认为笔迹潦草是书写者对读者不敬,是对收信人、编辑、排字工人缺乏尊重。因此,她写信总是笔迹清晰工整,寄给印刷所的手稿,则用印刷体字母誊写得清清楚楚。
回信,从不拖延。如果上午收到邮寄来的信件,往往立刻在笔记本里写出回复的草稿,仿佛列入当天的创作流程。她把写信也当成创作一样看待,几乎像对手稿那样严格挑剔。
一天当中,往往几次中断写作,然后又回到笔记本旁边。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连夜写作。
任何环境条件下,她都能写作,我想强调的是: 任何环境条件下。
吃苦耐劳、内在的组织能力跟她的诗歌才华是相辅相成的。
合上笔记本,推开自己房间的门——承受各种家务与日常操劳。
![图片[4]-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 终生孤独无助-人文百科](https://img2.jiemian.com/101/original/20160831/147262544681641200_a700xH.jpg)
父母亲的爱情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艾伏隆比她小一岁,出生于1893年,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9月26日(旧历)。
1911年5月5日,他们俩相遇了,谢廖沙十七,玛丽娜十八,相遇在科克捷别里空旷的海岸边,海滩上布满了砾石,离沃洛申居住的地方不远。玛丽娜收集好看的小石头,谢廖沙帮她寻找,小伙子像个大男孩儿,忧郁、温和,反倒增添了几分英俊(玛丽娜觉得他很快乐,更确切地说是——兴奋!),他的两只眼睛大得出奇,看到这样的眼睛,难免对未来心驰神往。玛丽娜心中暗想: 如果他能找到一块红玛瑙宝石,我就嫁给他!说来也巧,这样的红玛瑙他立刻就找到了,是用手摸索到的,因为他那双灰色眼睛一直凝视着她绿莹莹的明眸,他把挺大的一颗红玛瑙宝石放到她的手心里,粉红色的玛瑙晶莹剔透,她一辈子带在身边,流传至今,堪称神奇……
1912年1月,谢廖沙和玛丽娜举办了婚礼,从他们俩邂逅相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短暂的几年是他们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段安稳幸福的日子。
1914年,谢廖沙刚上莫斯科大学读一年级就遭遇战争,他以救护列车男护士的身份奔赴前线。他渴望投入战斗,不过受健康状况所限,难以参加阵地作战,只能一班接一班地执行医疗看护的任务。后来,他进入军官学校接受训练,这对他日后的遭遇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受到其他军官忠君保皇思想的感染,国内战争爆发后,他站在了白卫军阵营一边。信守誓言、信守战斗情谊,导致他很快走上了“白卫军运动”溃败覆灭的道路,走上了世界上最艰难、最悲惨的流亡之路,经过盖利博卢半岛和君士坦丁堡,辗转漂泊到捷克,以后又到了法国,像幽灵一样,没有国籍,没有公民身份,肩负着过去无比沉重的负担,一辈子将在痛苦与前途渺茫中度过……
国内战争那几年,我的父母几乎完全丧失了联系;始终不能通信,偶然得到的信息也是“捎信人”带来的口信或传闻,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未必可信。两个人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谁又能料到呢!多亏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即便玛丽娜这边得不到任何消息,她还是写出了颂扬“白卫军运动”的诗歌《天鹅营》,而那一边,她的丈夫,则一步步,一天天走向最后的溃败与逃亡。
当确信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跟溃败的白军将士一起流亡到了土耳其,玛丽娜拜托到国外出差的爱伦堡帮助她寻找丈夫;爱伦堡不负重托,找到了谢尔盖·雅可甫列维奇,经过长途跋涉,他已经到了捷克,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学生。玛丽娜当即决定——出国去跟丈夫团聚,既然他身为白军军官,在那个年代,要想返回祖国——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记得跟随母亲刚刚出国见到父亲后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听母亲朗诵了《天鹅营》组诗里的几首诗,父亲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痛苦,他说:“……玛丽诺奇卡,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兄弟残杀,是自杀式的战争,我们打仗,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对人民缺乏了解,我们自己觉得似乎是在为人民战斗。不是‘我们’为人民作战——而是我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为人民战斗。其他的人作战只不过为了把失去的东西从人民手里重新夺回来,重新得到多数人奉献给他们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之所在。的确有‘为信念、为沙皇、为祖国’的战斗,然而那些人遭到了枪决、绞刑和抢掠。”“不是还有英雄吗?”“的确有英雄。可惜,人民不承认他们是英雄。曾经作出的牺牲就更不必提了……”
“谢廖仁卡,您,您到底怎么啦?……”“是这样,您不妨想想,战争期间一个车站上的情景——这是个很大的枢纽站,站台上挤满了士兵、背着布袋的小商贩,妇女、孩子,一片惊恐,混乱不堪,拥来挤去,互相推撞拉扯,争先恐后想挤进车厢……你也裹挟在人群当中,第三遍铃声响了,列车已经启动——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上帝保佑!你总算上了火车,不料,你却在一瞬间意识到,你跟很多人一起,慌乱之中上错了火车,刹那间吓得要死……你的队伍开往另一个方向,要想回去已绝不可能——那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玛丽诺奇卡,要想回去,只有步行,——沿着枕木,走一辈子……”
这次谈话以后,玛丽娜写了抒情诗《铁轨上的黎明》。
此后我父亲的全部生活就是——沿着枕木往回走,走向俄罗斯,经过了数不清的坎坷、艰难、危险与牺牲,他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是祖国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弃儿。
![图片[5]-茨维塔耶娃逝世75周年:从不软弱无力 终生孤独无助-人文百科](https://img3.jiemian.com/101/original/20160831/147262462058959500_a700xH.jpg)
书摘部分节选自《缅怀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俄]阿里阿德娜·艾伏隆 著,谷羽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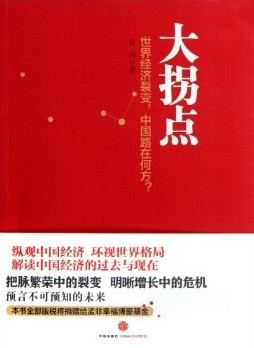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