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既然有维护自己的“生存要素”,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那么,就意味着同时拥有抵抗权、起义权和革命权。
有关生存权,埃弗里特在《农产品的销售》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既然人在国家里占有指定的地位或级别,那么每个人就都有权要求国家为他提供维持生计的手段。任何妨碍这一生存权的交易和契约,不管是如何达成的,都是不公平、无效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权最终要诉诸社会(相对于经济)的责任。”
生存权是最起码的权利,有的政府却把它当作人民的全部权利。国家的所有资源都由政府或相关者垄断了起来,不让人民有自由发展和创造财富的空间,从而形成国富民穷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这样的政府是从来不承认人民有抵抗权的,只要出现自发的群体性行动即厉行镇压,国家的反动性在这里表露无遗。于是,人民只好长此屈辱地生存,为生存而生存。
如果人民失去合法的抵抗权,可以想见,所有写进“契约”(包括宪法)中的属于人民的“权利”都是虚假的,乌有的。
抵抗权是基本人权之一。它承认对侵犯人权的非法国家权力、非法的法和野蛮执法的暴行进行抵制和反抗的权利。
古典自然法学家斯宾诺莎、格老秀斯早已论及人民反对违背正义的人立法的正当性,洛克则明确提出有关抵抗权和革命权的主张,十八世纪的人权理论,是在革命的炽热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其核心就是反对专制政府的抵抗权。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1793年宪法都曾宣布“当暴虐的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反抗压迫”是一项“不可转让”的人权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这是关于抵抗权作为法定权利的最早文件。
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劝告人们在行使抵抗权时要谨慎从事,不可因为“暂时的原因”而轻易投入创伤性的革命,但是,他仍然不得不承认:当人们遭受专制政权的迫害时,革命不但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
卢梭本着“正义即公意”的原则,这样解释人民的抵抗权:“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他提出人民直接行动的理论,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声辩说,从政府篡夺了主权并被用来压迫人民的时候起,社会契约就被破坏了,每个公民因此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包括以暴力推翻暴君的自由。马布里并不认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赞同人民主权论,他从中引出武装反抗暴政合理性的结论说:“公正的原则允许人民拿起武器,反抗破坏法律或滥用法律来窃取无限权力的压迫者。”
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义权写进了宪法。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说:“当一个民族被迫诉诸起义权时,对暴君来说,这个民族便回到了自然状态。暴君已经毁了公约,怎么还能引用社会契约呢?……暴政和起义的结果,就是彻底终止与暴君的一切契约,暴君与人民之间重新处于战争状态。”
抵抗权是从人权及人民主权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它可以作为法定权利,即合法的抵抗权;但又可以是“法外的抵抗权”,即针对人定法的非法而采取的法外权利进行反抗的抵抗权。它反对政府现行的“非法之法”,却符合“法上之法”——人权与正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
在东方,著名的“布拉格之春”的主角之一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说:“人民不满意党的领导。我们无法改变人民,所以我们改变了领导人。”在西方,参与反抗运动的麦龙·马格尼特在其著作《梦想与梦魇》中说:“任何社会的主要功能是保障社会契约的执行。如果社会合法的权力机构变得腐败时,除了无政府状态,你还能期待什么?”
摘自《革命寻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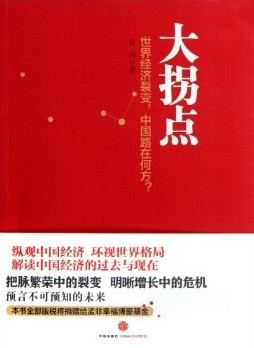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