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家论及社会契约,所指实际上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评价一个政权,主要看政府如何履行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当然,首先得看它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然后才是它的职能和绩效之类。政府有没有合法性?它从何处获取统治的权利?答案不能看它的公告和宣言,而要看人民的态度,看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是否首肯。
对此,选举是唯一的考量方式。
以现代民主的眼光看,权力并非神授,也非继承(文革发生后有“接班人”之说,实质上是变相的继承),而是来源于民众的选举。所以,凡称民主国家没有不重视普选一项的。
“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在1819年召开的一次委内瑞拉国会开幕演说中就指出政治危机起于独裁,惟有选举和更换领袖才能加以克服,说:“受民众拥护的政体必须不断地进行选举,因为再没有比允许同一位公民长时间掌权更危险的事情了。”而在专制国家,领袖的终身制是受宪法保护的。
1838年,在英国,伦敦工人协会发布《人民宪章》,提出关于成年男子普选权等多项政治要求,酿成著名的“宪章运动”。虽然运动遭到镇压,但是,普选权作为基本人权终于为政府所承认。当时,马克思对运动表示热烈的支持,撰文说普选权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工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他说:“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恩格斯也指出,“‘合法发展’和‘普选’必然导致一场革命。”后来,他仍坚持认为,普选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只是对实现普选没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成以后,竟然可以抛弃“普选”制而采用“代表”制。
“人民主权”是一个乌托邦,其实普选只是走向乌托邦的第一步。在政治实践中,要使社会不为国家所吞并,道路遥远而艰难。
“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大约在近代同一时期产生。像古希腊不存在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政府与教会分享统治权力,都说不上国家主权;但是,人民同样处于无权者状态,所谓“主权者个人”是没有的。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在“国家回归”中,国家主权乃成为一种制度性现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民族的名义下,大大扩展自身的功能,尤其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国家主权”的论调在国际政治间得到广泛的应用,强化了国家的权威性,以致在国家内部,国家主义的主权观,被传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种普遍意志,对脆弱的民主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
国家通过垄断合法强制力,以保持对现有秩序的有效控制。从时间上看,国家愈来愈强势是明显的。
所谓“国家主权”,到底是谁授予的?居然是国家自己!这就是政治学者辛西娅·韦伯讽刺说的“自我指称的荒谬”。
国家是众多政治共同体之一,“人民”则只有一个。人民是当然的主权者,只有承认“人民主权”,自由、民主、自治才能获得切实的保证。首先,人民把权力移交给国家,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权威,有了使用权。在国际领域,所谓国家主权,实质上是国家以实体的身份代表本国人民行使自主的权利,如同在本国事务中政府代为行使管治权一样。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决议中的“人道主义干涉”、“人权大于主权”才有了成立的根据。
从表面上看,国家是中立的,它的存在在于调节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维持和平秩序,保证公平竞争,同时也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国家集团拥有自主性的结构,也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当它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加以利用时,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支配阶级的利益,尤其在危机时期;但是从根本上,与支配阶级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因此能够较长期地结成政治同盟,而以牺牲被支配阶级的利益为共同目标。
这样,国家就失去了正当性,加以自身的腐败,政治危机将随之发生。不过,即使群体事件大小多如牛毛,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甚至重大的政治动乱陡然而至,声势浩大,只要国家的强制性组织军队、武警等还掌握在统治集团手里,且未失去固有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政权的稳定性就仍然可能得到保证,哪怕它已经千疮百孔。
所以,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应当是正义高悬如阳光普照的社会。博丹把共和国称为“一个正义的政府”,就是这个意思。
正义的政府,使公平地对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成为可能;同时,能够自行约束自身的政治权力。非正义的政府倒行逆施,不但高度掌握权力,聚敛财富,而且动辄以“国家理由”侵犯个人权利,人为制造社会鸿沟,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古罗马基督教教会作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指出:“没有了正义,国家不过是一大群强盗。”书中还载有亚历山大大帝与被俘的海盗的一段对话:国王问,为什么要占领海面?海盗回答说,你要抢占的是整个地球,只是因为我的战舰太小,所以叫我海盗;因为你有巨大的战船,所以称为统帅。这段对话,与我国《庄子》中说的“彼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颇相似。
保罗·利科强调正义的重要性,打比方说:“正义的独立行使和民意的独立形成,是政治上健康的国家的两个肺,否则就会窒息。”他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正在于权力垄断,扼杀了正义、自由和民主,致使社会窒息所致。
专制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说: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首都巴黎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四十年来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同时,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要原因。
他明确指出,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也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然得以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性,正在于此。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之后,列宁承认说:“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其中盛行“糟糕之极的前资本主义文化”。显然,列宁试图拒绝这笔旧制度的遗产,而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专制主义文化具有浓厚而强烈的发酵性,从历史的情况看,这其中不但有沙皇制度的遗留,而且带有所谓“工农专政”的时代性病症,其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具有一种创新性。
至斯大林时代,权力空前集中,政治学者把这种二十世纪的现代专制主义称作极权主义。
在长期从事权力研究的福柯看来,权力这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型的性格,含有敌对和冲突的反社会动机。国家权力作为最大的权力,它与社会的潜在的或是现实中的冲突无疑是巨大的,那么将依靠什么维持自身的稳固的存在呢?
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格尔和詹森认为,政府的权力稳定姓,依赖社会的心理倾向和大众的支持。国家必须让社会保持一种共识,格尔强调功利性共识,詹森强调价值共识,都是通过共识的凝聚,以体现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即使要动用暴力,也必须建立在大众共识之上,而不是有组织的强制力可以奏效的。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则强调国家的有组织的强制力的作用。列宁是鼓吹暴力革命的,他的《国家与革命》对于国家的定义也是强制性的,暴力的,他宣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除此,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托洛茨基肯定说:“每个国家都是奠基于暴力”,还补充说,“确实如此。”他明确说国家是建立在合法——也即宣称为合法——的暴力手段上的人对人的统治。蒂利对政府的界定是“由特定人口集中控制着主要强制手段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认为,国家能够压制民间力量和革命行动,对于革命的成功的解释,他们也都把重点放在旧政权所垄断的强制力的崩溃和新政权对武装力量的建设之上。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六章名为“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说明暴力的观念、形式和行为乃由旧制度传承而来,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教育的产物。
他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专制制度”,指出路易十四以后的旧制度的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他指出,政府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灌输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喜好暴力。政府一直在开办这类学校,给予下层阶级以一种暴烈的、冒险的教育。他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在评论中对大革命同旧制度进行类比,突显的是权力中的强制力的共性。他着眼于政治形式方面,暴力也是一种形式,而容易模糊新旧不同政治体的内容。
但是,无论如何,国家主权至上是值得警惕的。
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论述洛克的思想时说,洛克把国家视作人类的、乃至人为的发明,他不相信人类会向它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利,除非以一种事先有担保的回报作为条件。权力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仲信托,会因滥用而被撤回,正像十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认为的那样。
如果人民不肯向国家出让自己的权利,或者已经出让而遭到滥用的时候,怎么办?除了革命,是否存在别的出路?
摘自《革命寻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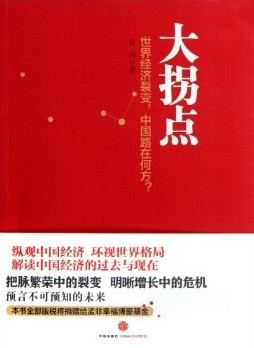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