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大家都很任性”》的报道说,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应反腐问题时表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用网络热词,“大家都很任性”。译员当时与发言人沟通,询问“大家都很任性”是什么意思。这虽然不过是一则“花絮”报道,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话语中使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作清晰的表述。
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任性”是一个贬义词,说一个人任性,是指他由着性子,没有约束、放纵胡为、不负责任。说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任性”,会让人以为,这样的反腐是随意胡来,既无道德依据也无司法章程,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难怪翻译会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
翻译必须是认真的,要吃透了说话者的意思才能正确地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认真的翻译必定不能“任性”。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是因为说话者自己太任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弄得别人摸不透他的意思——“反腐”是一件好事,怎么用“任性”这个贬义词来说明它的成就呢?怎么能说反腐是任意胡来呢?
其实“任性”本来是很容易翻译的(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 do)。翻译无从下手,不是因为她缺乏能力,而是因为说话者太随意,忽视了公共话语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包容性”。
在美国,公共说理教学课上都会向学生介绍使用“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重要性。既然是在公共场合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那就应该清楚明了地让大家能听懂。这不仅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交谈伦理的问题。“不包容”的实际效果就是“排斥”,例如,如果在场的人都是中国人,有的懂英语,有的不懂,那就应该说汉语。如果必须使用英文的某个专门说法,那就一定要提供一个汉语的翻译。
即使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之间,也有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最常见的排斥性语言就是“俚语”(slang)和“行话”(jargon)。老师会要求学生,在公共发言时不要使用俚语和行话,因为这样的语言只是在特殊的人群中使用,其他许多人会因为听不懂,而被实际排除在语言交流之外。
网络上的“任性”,如果它的意思与大多数人在规范语言中所说的意思不合或相矛盾(如贬义变成了褒义),那么,它就是一个“俚语”。“任意”这个俚语是在特定小群体中使用的语言,使用它的人数再多,与使用汉语的整体人群相比,也毕竟是小群体。 更重要的是,俚语是一种非规范的语言。语言学家Bethany K. Dumas 和 Jonathan Lighter甚至将俚语称为一种“故意的误用”。
另一种具有排外性的小群体语言是“行话”(jargon),如医生、律师、专业人士之间使用的特殊语言(词汇或说法)。医生们之间讨论一个病人的病情或治疗可以用行话。但是,如果要对病人作出解释和说明,就需要用病人听得懂的语言,不然就会把病人实际排除在交流之外,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用病人听不懂的话在忽悠他。
“俚语”往往很难翻译,因为俚语的说法不仅仅有一个“意思”,而且带着某种难以传达的态度、情绪、姿态、好恶。语言学家Michael Adams称俚语为一种“阈限语言”(liminal language),换句话说,是一种处于意识边缘的,勉强感觉得到的语言。他指出,“就算是有语境,也经常不可能说清一个俚语的用意和弦外之音。”
几年前,“不折腾”这个俚语被用作一个新政治词汇的时候,也碰到了怎么翻译的问题。有人试图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英语,其中有我的同学或老熟人,他们英语都挺棒,但却还是无法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贴切的英语。与贬义仍然是贬义的“不折腾”相比,贬义变成了褒义的“任性”更是一个翻译的难题。 政治人物在公共发言时使用俚语往往不是为了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而是表示一种姿态,如亲民、幽默、随和,以此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获得他们的好感等等。但是,公共语言中运用俚语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会让本该说清的问题停留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让人勉强感觉好像是某个意思。而且,它还会给公众留下耍嘴皮子、言虚不言实的不良印象。为了避免把严肃的公共问题娱乐化,避免把公共论述变成一种娱乐化的政治,有必要重视公共话语中的俚语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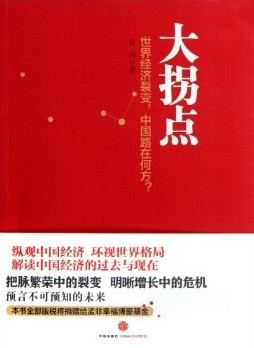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