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年 11 月 26 日-1913 年 2 月 22 日)是瑞士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为20 世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许多重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和符号学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一起)
他的翻译者之一罗伊·哈里斯 (Roy Harris ) 总结了索绪尔对语言学和“人文科学的整个范围”研究的贡献。它在语言学、哲学、精神分析、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尤为突出。尽管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扩展和批判,但索绪尔引入的组织维度继续为当代处理语言现象的方法提供信息。正如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在回顾《库尔斯》后所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语言科学的理论基础”。
![图片[1]-费迪南·德·索绪尔-人文百科](https://www.rwpedia.com/wp-content/uploads/2023/03/image-8.png)
传记
索绪尔1857 年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亨利·路易斯·弗雷德里克·德·索绪尔 (Henri Louis Frédéric de Saussure ) 是矿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分类学家。早在十四岁时,索绪尔就表现出相当的天赋和智力。1870 年秋天,他开始就读于日内瓦的 Martine 学院(前身为 Lecoultre 学院)。在那里,他与同学 Elie David 的家人住在一起。索绪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原本打算在日内瓦中学继续学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在十四岁半时还不够成熟,而是把他送到了日内瓦学院。索绪尔很不高兴,他抱怨说:“我进入了日内瓦学院,在那里浪费了一年,就像可以浪费一年一样。”
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梵语并学习了各种课程后,他于 1876 年开始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研究生。
两年后,21 岁的索绪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印欧语系原始元音系统的备忘录》(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的书。此后,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了一年,师从私教海因里希·齐默 (Heinrich Zimmer)学习凯尔特语,师从赫尔曼·奥尔登堡 (Hermann Oldenberg)继续学习梵文。他回到莱比锡为他的博士论文De l’e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进行答辩,并于 1880 年 2 月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搬到了巴黎大学,在那里他讲授梵语、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偶尔也讲授其他科目。
Ferdinand de Saussure 是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语言学家之一,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他本人一生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甚至他的几篇科学文章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他关于立陶宛语语音学的出版物主要取自立陶宛研究员弗里德里希·库尔沙特Friedrich Kurschat的研究,索绪尔于 1880 年 8 月与他一起在立陶宛旅行了两周,并且索绪尔读过他的(德文)书籍。索绪尔在莱比锡学习了立陶宛语的一些基本语法一个学期但不会说这种语言,因此依赖于 Kurschat。
索绪尔在高等研究学院任教十一年,期间他被授予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892 年在日内瓦获得教授职位后,他回到了瑞士。索绪尔余生都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直到 1907 年,索绪尔才开始教授普通语言学课程,他开设了三期课程,并于 1911 年夏天结束。他于 1913 年在瑞士沃州的 Vufflens-le – Château去世。他的兄弟是语言学家和世界语学家勒内·德·索绪尔,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索绪尔 ( Léopold de Saussure)。他的儿子雷蒙德索绪尔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
索绪尔在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的不同时期,试图写一本关于一般语言学问题的书。他于 1907 年至 1911 年间在日内瓦发表的关于语言描述的重要原则的讲座被他的学生收集并于 1916 年在著名的 《通用语言大道》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出版。他一生发表的作品包括两部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和笔记,所有这些都收集在 1916 年出版的约 600 页的卷中。索绪尔没有发表任何关于古代诗学的著作,即使他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本。让·斯塔罗宾斯基 (Jean Starobinski)在 70 年代编辑并展示了他们的材料,此后还出版了更多内容。他的一些手稿,包括 1996 年发现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发表在《普通语言学著作》上,但其中的大部分材料已经在 1967 年和 1974 年恩格勒的《课程》批评版中发表。今天看来很明显《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所谓的编辑 Charles Bally 和 Albert Sèchehaye,而且各种细节很难追溯到索绪尔本人或他的手稿。
工作和影响
索绪尔对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的理论重建,特别是他的喉音理论,在当时未经证实,在后世语言学家如埃米尔·本韦尼斯特和沃尔特·库弗勒的著作中破译赫梯后取得了成果并得到了证实,他们都从阅读 1878 年的备忘录中获得了直接灵感。
索绪尔对 20 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概念被纳入结构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他对结构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关于语言的两层现实理论。第一个是语言langue,抽象和无形的层,而第二个是口语parole,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实际语音。这个框架后来被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采用,他使用两层模型来确定神话的真实性。他的想法是,所有的神话都有一个潜在的模式,这些模式形成了使它们成为神话的结构。这些为文学批评确立了结构主义的框架。
在欧洲,索绪尔死后最重要的工作是由布拉格学派完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尼古拉·特鲁贝茨科伊和罗曼·雅各布森领导了布拉格学派的努力,在194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确立了语音学理论的进程。雅各布森的通用化结构功能音韵学理论,基于独特特征的标记层次,是根据索绪尔假说对语言分析平面的第一个成功解决方案。在其他地方,Louis Hjelmslev和哥本哈根学派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提出了对语言学的新解释。
在美国,“结构主义”一词变得非常模糊,索绪尔的思想影响了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的分配主义,但他的影响仍然有限。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被认为牢固地基于索绪尔符号原理的理论,尽管有一些修改。Ruqaiya Hasan将系统功能语言学描述为“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Michael Halliday认为:
索绪尔把符号作为语言结构的组织概念用短语“l’arbitraire du signe”来表达语言的常规性质。这实际上具有突出系统中任意一点的效果,即单词的音位形状,因此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其余部分的非任意性。一个明显非任意性的例子是语言中不同种类的意义由不同种类的语法结构表达的方式,正如当语言结构用功能术语解释时出现的那样。
普通语言学课程
索绪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普通语言学课程》 (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 于 1916 年由以前的学生查尔斯·巴利 (Charles Bally )和阿尔伯特·塞切哈耶 ( Albert Sechehaye ) 根据索绪尔在日内瓦的讲座中的笔记在死后出版。《课程》成为 20 世纪最具开创性的语言学著作之一,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许多想法在其他 20 世纪语言学家的作品中已经预见到),而是因为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现象时采用的创新方法
它的核心概念是,除了实时生产和理解的混乱辩证法之外,语言可以被分析为一个由不同元素组成的形式系统formal system。这些元素的例子包括他的语言符号概念,它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尽管符号也可能有指称referent,但索绪尔认为那超出了语言学家的权限范围。
在整本书中,他表示语言学家可以对文本或语言理论进行历时分析diachronic analysis,但必须尽可能多或更多地了解语言/文本在任何时刻(即“同步synchronically”)存在的情况:“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活的科学,是社会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研究一切可以作为符号的东西,他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
语言学之外的影响
结构主义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后来被罗兰·巴特、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法国知识分子应用于不同领域。这些学者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别是文学研究/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受到索绪尔思想的影响。
语言视图
索绪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理论。一方面,语言是符号系统;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共同体的产物。
作为符号学的语言
双侧符号The bilateral sign
索绪尔对符号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他所谓的符号学,双边(双面)符号的概念,它由“能指”(一种语言形式,例如单词)和“所指”(形式的含义)组成。索绪尔支持符号的任意性的论点,尽管他没有否认某些词是拟声词的事实,或者声称像图一样的符号是完全任意的。索绪尔也不认为语言符号是随机的而是历史巩固的。总而言之,他并没有发明任意性哲学,但对它做出了非常有影响的贡献。
不同语言的词的任意性本身就是西方语言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语言是自然的还是任意的(以及人为制造的)这个问题在启蒙时代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再次出现,当时中世纪的经院教条,即语言是由上帝创造的,受到了人文主义哲学的拥护者的反对。人们努力在失落的亚当语言的基础上构建一种“通用语言” ,并进行了各种尝试来发现所有人都能轻松理解的通用单词或字符,无论其国籍如何。另一方面,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那些相信语言是人类理性创新的人之一,并主张单词的任意性。
索绪尔在他的时代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人质疑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然而,他不同意每个词都对应于“它所命名的事物”或现代符号学中所谓的指称物的普遍观念。例如,在索绪尔的概念中,“树”一词并不是指作为物理对象的树,而是指树的心理概念。因此,语言符号源于能指(“声像”)和所指(“概念”)之间的心理联系。因此,没有意义就没有语言表达,没有语言表达就没有意义。因此,后来被称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包含了语言相对性的含义。然而,索绪尔自己的观点却被描述为语义整体论的一种形式,它承认语言中术语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只是在方法论上将语言术语与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括起来。
光谱颜色的命名说明了意义和表达是如何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同时产生。不同的颜色频率本身毫无意义,或者仅仅是物质或潜在的意义。同样,与任何内容无关的音素组合也只是无意义的表达潜力,因此不被视为符号。只有当光谱的一个区域被勾勒出轮廓并被赋予一个任意名称,例如“蓝色”时,标志才会出现。符号由能指(“蓝色”)和所指组成(颜色区域),以及连接它们的关联链接。由于意义潜能的任意划分,所指不是物理世界的属性。在索绪尔的概念中,语言最终不是现实的功能,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因此,索绪尔的符号学包含了符号学的双边(two-sided)视角。
同样的想法适用于任何概念。例如,自然法并没有规定哪些植物是“树”,哪些是“灌木”或不同类型的木本植物;或者这些是否应该被分成更多的组。与蓝色一样,所有符号都获得与系统其他符号(例如红色、无色)相反的语义值。如果出现更多符号(例如“marine blue”),则原始词的语义范围可能会缩小。相反,词语可能会过时,从而减少对语义领域的竞争。或者,一个词的意思可能会完全改变。
在他去世后,结构和功能语言学家将索绪尔的概念应用于受意义驱动的语言形式分析。另一方面,语言表达产生概念系统的相反方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构主义者的基础,他们采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概念作为所有人文科学的模型,研究如何语言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因此,索绪尔的模型不仅对语言学很重要,而且对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重要。
对立理论Opposition theory
第二个重要贡献来自索绪尔基于对立原则的语言组织概念。索绪尔区分了意义meaning(significance)和价值value。在语义方面,概念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对比而获得价值,从而创建一个概念系统,用现代术语来说,该系统可以描述为语义网络。在声像层面,音素和语素通过与相关音素和语素的对比获得价值;在语法层面,词性通过相互对比来获得价值。每个系统中的每个元素最终都与不同类型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元素进行对比,因此没有两个元素具有完全相同的值:
“在同一种语言中,所有用来表达相关思想的词都相互限制;法语redouter ‘dread’、craindre ‘fear’ 和avoir peur ‘be afraid’ 等同义词只有通过它们的对立才有价值:如果redouter不存在,它的所有内容都会流向它的竞争对手。”
索绪尔用二元对立来定义自己的理论:符号—所指(sign—signified),意义—价值(meaning—value),语言—言语(language—speech),共时—历时(synchronic—diachronic),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internal linguistics—external linguistics),等等。相关术语标记表示二元对立之间的价值评估。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等战后结构主义者对这些进行了广泛研究,以解释社会概念化的组织,后来被后结构主义者批评。认知语义学在这一点上也与索绪尔不同,它强调相似性在定义头脑中的类别以及对立方面的重要性。
布拉格语言学界以标记理论为基础,在语音学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将其改造成系统的音位学研究。尽管对立和标记性这两个术语与索绪尔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概念正确地联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发明在他之前被许多 19 世纪语法学家讨论过的术语和概念。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
索绪尔将语言视为“社会事实”,触及了在他那个时代有争议的话题,这些话题将继续在战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引起意见分歧。索绪尔与 19 世纪语言理论的关系有些矛盾。其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Völkerpsychologie或Volksgeist思想,这些思想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伪科学。
然而,索绪尔认为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对待这些想法是有用的。他没有抛弃奥古斯特·施莱歇尔的有机主义或海曼·施泰因塔尔的“民族精神”,而是以旨在排除任何沙文主义解释的方式限制了它们的范围。
有机类比,Organic analogy
索绪尔利用语言作为活有机体的社会生物学概念。他批评奥古斯特·施莱歇尔 August Schleicher 和 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 将语言视为为生存空间而斗争的有机体的观点,但只要对语言“有机体”的研究不包括其对领土的适应性,他就坚持将语言学作为自然科学来推广。这一概念在后索绪尔语言学中被布拉格圈子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尼古拉·特鲁贝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修改,并最终消失。
语音回路,The speech circuit
也许索绪尔最著名的思想是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language and speech),“言语”指的是语言使用的个别出现。with ‘speech’ referring to the individual occurrences of language usage.这些构成了索绪尔“言语回路”(circuit de parole)的三个部分中的两个部分。第三部分是大脑,即语言共同体个体成员的头脑。这个想法原则上是从斯坦塔尔那里借来的,所以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概念与“人民主义者”相对应,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任何民族主义的解释。在索绪尔和涂尔干的思想中,社会事实和规范并没有提升个人,而是束缚他们。索绪尔对语言的定义是统计的而不是理想化的。
“在通过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个体中,将建立某种平均数:所有人都将复制——当然不是完全正确,而是近似地——结合相同概念的相同符号。”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一套与言论有关的常规规则或规范。当至少有两个人进行对话时,每个说话者的思想之间就会形成一个交流回路。索绪尔解释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既不存在于言语中,也不存在于思想中。它只适当地存在于循环内的两者之间。它它位于语言群体的集体思想中,并且是其产物。个人必须学习语言的规范规则,并且永远无法控制它们。
语言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分析语音样本来研究语言。出于实际原因,这通常是对书面文本的分析。通过文本研究语言的观点绝不是革命性的,因为自语言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普遍的做法。索绪尔并不反对内省,并且在没有参考文本语料库中的来源的情况下使用了许多语言示例。然而,在索绪尔的当代语境中,语言学不是心灵研究的观点与威廉·冯特 ( Wilhelm Wundt ) 的 Völkerpsychologie 相矛盾;在后来的背景下,生成语法和认知语言学。
意识形态争论的遗留问题
结构主义与生成语法
索绪尔的影响在美国语言学中受到限制,美国语言学由威廉·冯特的语言心理学方法的倡导者主导,尤其是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布卢姆菲尔德学派拒绝索绪尔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社会学甚至反心理学(例如路易斯·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吕西安·特斯涅尔Lucien Tesnière )语言理论方法。有问题的是,后布卢姆菲尔德学派被昵称为“美国结构主义”,引起了混乱。尽管布卢姆菲尔德在他1933年的教科书《语言》中谴责了冯特的弗尔克心理学,并选择了行为心理学,他和其他美国语言学家坚持冯特将语法对象作为动词短语的一部分进行分析的做法。由于这种做法不是语义驱动的,他们主张语法与语义的脱节,-从而完全拒绝结构主义。
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宾语应该出现在动词短语中,这个问题困扰了美国语言学家数十年。后布卢姆菲尔德方法最终被诺姆·乔姆斯基改革为社会生物学框架,他认为语言学是一门认知科学;并声称语言结构是人类基因组随机突变的表现。新学派生成语法的倡导者声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已经被乔姆斯基的现代语言学方法所改革和取代。Jan Koster断言:
毫无疑问,直到 1950 年代,索绪尔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本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但他在当前的语言理论思考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作为乔姆斯基革命的结果,语言学经历了一系列概念转变,这些转变导致了各种技术上的先入之见,远远超出了索绪尔时代的语言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索绪尔似乎已经正确地陷入了近乎遗忘的境地。
然而,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认为存在各种误解。他指出,乔姆斯基对“结构主义”的批评是针对布卢姆菲尔德学派的,而不是该术语的正确称呼;并且结构语言学不应被简化为纯粹的句子分析。
索绪尔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课程以对 19 世纪语言学的批评开始和结束,其中他特别批评了大众精神Volkgeist思想和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及其同事的进化语言学。索绪尔的思想取代了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逐出人文学科。
理查德·道金斯 ( Richard Dawkins)于 1976 年发表的模因学 ( memetics)使达尔文的语言单位作为文化复制者的观念重新流行起来。这一运动的追随者有必要以一种同时反索绪尔和反乔姆斯基的方式重新定义语言学。这导致了沿着达尔文主义路线重新定义旧的人文主义术语,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通过以激烈的语气为标志的辩论。在《自私的基因》之后几十年的功能主义-形式主义辩论中,攻击索绪尔遗产的“功能主义”阵营包括诸如认知语言学、结构语法,基于用法的语言学和新兴语言学。威廉·克罗夫特William Croft主张“功能类型学理论”,批评索绪尔的使用或有机类比:
在将功能类型学理论与生物学理论进行比较时,必须注意避免对后者进行讽刺。特别是,在将语言结构与生态系统进行比较时,我们不能假设在当代生物学理论中,人们认为有机体对处于平衡状态的生态系统内的稳定生态位具有完美的适应性。将语言类比为一个完美适应的“有机”系统,其中有生命是结构主义方法的一个特征,并且在早期结构主义著作中很突出。面对生物体的非适应性变异和相互竞争的适应性动机的经验证据,生物学中关于适应的静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结构语言学家亨宁·安徒生不同意克罗夫特的观点。他批评模因学和其他文化进化模型,并指出“适应”的概念在语言学中的含义与生物学中的含义不同。埃萨·伊特科宁 Esa Itkonen和 雅克·弗朗索瓦Jacques François同样为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观念辩护;代表布拉格语言界的Tomáš Hoskovec托马斯·霍斯科维奇 解释并捍卫了索绪尔的观点。
相反,其他认知语言学家声称要继续并扩展索绪尔在双侧符号方面的工作。然而,荷兰语言学家 Elise Elffers 认为,他们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与索绪尔自己的想法不相容。
“结构主义”一词继续在结构- 功能语言学中使用,尽管有相反的主张,但它仍将自己定义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语言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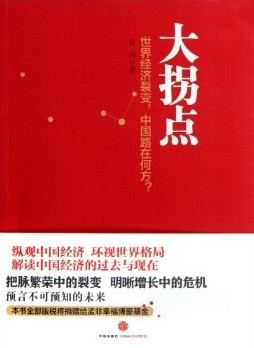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